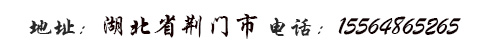摘录和随感北岛时间的玫瑰
|
北京皮肤病最好的医院 http://pf.39.net/bdfyc/140106/4322698.html ↑↑↑点击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P43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写到他对革命的预感:“是的,我用远处田野上脱粒机那警觉的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倒下而膨胀!”“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年在彼得堡,曼德尔施塔姆见证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年,他随政府机构搬到苏维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诗出现在11月15日苏维埃报纸《人民自由报》上,另一首诗出现在年5月2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年至年内战期间,他四处漂泊,曾被不同的阵营抓获。……P53-54 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级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20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所谓“解放”,其实是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而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到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P59 列宁在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P60 西方的不少传记和文章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而事实上,20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战场上。”P61 (娜杰日达:)“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知不多的人对他的生活往往会简单地图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没有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会那么注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用他的价值尺度去掂量它们。若他简单地背对现实,生活和调整就容易多了。这对M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像他的同时代人穿过同样的生活通向逻辑的终点。” 年,在苏联第45期《读者与作家》杂志题为“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的调查表上,曼德尔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精神的供给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债务人,但我也在带给它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P63 他(赵一凡)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吴注:很多人为“安得广厦”这几句感动不已。但所谓“天下寒士”,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或所有在寒风中无屋可居无衣蔽体的人,而只是“贫寒”之“士”,也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 北岛早年力倡诗歌和政治分开,但早期的部分“政治”诗是他最有份量的作品。不过,也许如北岛所说:(诗人、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这本书里,北岛很注意自己所写的这些诗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政治触觉的退化事实上伴随着知识份子思想水平的退化,使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同样糊里糊涂,瞎子摸象。韩××有篇文章谈到:二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都有意地把“大师”们的政治倾向遮掩起来,模糊掉了…… 北岛在《革命与雏菊》一文中谈及尼加拉瓜革命。他写到自己跟那位仇视革命的外国朋友争辩,批判美国扮演的角色……但最后,革命的“堕落”也增添了他的灰心和茫然,在“革命与专制”之间彷徨失路,结论无非“权力使人腐化”,不能碰,不能夺取(也不能最终消灭)。这世界上可以落脚的地方,大概就只有“边缘的自我”了。 这篇写曼德尔施塔姆的,也在仔细辩析诗人和俄国革命的关系,对革命的态度演变。他试图祛除对革命的“简单的”敌意,引用列宁“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带有更明显的“更进一步”的“进步”愿望。文中还提到年初赵一凡“锒铛入狱”,自己因被卷入而产生恐惧:“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综观全文,以至全书,北岛对“革命”宛似带着一种“怅惘之情”。 从沙俄时代农奴制的废除直到二十世纪初“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云云,显然在持以对照当下。】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死亡赋格》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阿多诺终于收回他的那句格言:“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年5月法国学生的暴动,激发了策兰的政治热情。他独居,常回去看刚满13岁的儿子。策兰带他一起到街上散步,用多种语言高唱《国际歌》和别的革命歌曲。艾瑞克为父亲骄傲。P 回到巴黎后,有一天他和朋友沃姆(FranzWurm)坐地铁。沃姆后来回忆说:“有人从我们后面一伙年轻人中跳出来,低声吼着:‘让犹太人进烤炉吧!’只见他的脸绷紧,越来越悲哀,攥住拳头。”他们随后去邮局。邮局职员一看策兰的航空信是寄往以色列的,就故意把信揉皱,再扔进邮件堆中。…… 策兰住在塞纳河米拉波桥附近,这桥因阿波利奈尔的诗而闻名。年4月20日左右,策兰从桥上跳下去,没有目击者。……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了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P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帕斯捷尔纳克:)“那些作家的声音如雷霆一般,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与20世纪那些肤浅的艺术家相反,以我父亲为例,他的每幅画用了多大的努力呀!在20世纪我们的成功部分是由于机会。我们这代人的发现自然而然成为历史的焦点。我们的作品受命于时代。它们缺少普遍性:现在就已经过时了。另外,我相信抒情诗已不再可能表现我们经历的广博。生活变得更麻烦,更复杂。在散文中我们能得到表达得最好的价值……”P 鲍里斯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年冬天,斯大林召集帕斯捷尔纳克、叶塞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三个诗人,询问关于把诗歌从格鲁吉亚文(斯大林的母语)翻成俄文的问题。这是鲍里斯惟一一次与斯大林面对面。他在晚年回忆时描述道:斯大林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螃蟹般的侏儒,有一张黄色麻脸和翘起来的唇须”。而就在那一时期,他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歌。P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张枣:谁都知道,用韵律写作的俄文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而您几乎不用韵,这是为了反抗官方话语美化生活的企图吗? 艾基:不是几乎不用,而是从来不用。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它要的是没有生气的词和人。但诗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表达的人和物得是活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象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但它总是有一个极点的,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外在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一般来讲,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 …… 张枣:诗人能够既是政治动物又写纯诗吗?比如茨维塔耶娃? 艾基: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美妙的诗人,但就意识形态而言,她才幼稚呢。有一天她写了首《献给白军的神》的诗,一部拥护君主制度的作品,她丈夫,一名白军军官,回家后看了说,马丽亚,你什么都不懂,白军的神可真是天灾人祸。……P- 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是从语言内部开始的。……正是在高度集权的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迫害压力下,艾基创造了一种“隐微写作”,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P- 我和戈林娜(艾基的妻子)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从《母亲》到《喀秋莎》,从《小路》到《共青团员之歌》。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那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的眼中也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突然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都不怀念那个时代。”P 【吴注:艾基,也许是比较典型的“极权主义”之下知识份子的反抗样板,他解释自己不用“韵律”的理由,也许适合他自己,但就艺术来说只能是特例。他有意无意地把韵律跟专制扯在一起,来提升自己“从来不用”韵律写诗的意义时,这就把道理“拔高”到“上纲上线”的程度了。 “从语言内部开始”的“解构”,甚至于这种“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诚然是过份夸大。这种最典型的知识份子自辩之词,泛滥于中国的真假“精英”中。】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问:你是否在写诗前等待一种自发冲动?如果是的话,它是词语的还是视觉的? 答:写诗对我来说,是建立一个正规的词语密封舱,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最好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支柱(即叙述性),多少支撑那来自创造性身心的真正动因。动因总是在那儿,总是需要具体表达出来。对我来说,诗歌“冲动”或“灵感”只不过是突发的,通常是体力上的,如同能工巧匠的那种技艺。最懒的工人冲动最少。反之亦然。 问:你是否支持任何政党或政治经济信条? 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 问:作为一个诗人,你觉得什么使你区别于一个普通人? 答:所有的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动因,我只不过用诗歌这种媒介来表达而已。(P-) 他在给《年最佳诗选》的编辑的信中指出,他选的都是最糟糕的诗作,“对诗歌的智性阅读是有害的;一首从另一首吸血;两种相近的才能最易于互相抵消。”在给两个青年诗人的两本诗集写的书评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即使报以最大的同情,这样的诗人还是应该每周被踢一顿屁股。” 时间的玫瑰北岛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附录 ◆◆◆◆ 文革·北岛·“思想启蒙” ◆◆◆◆ 作者│吴季〔说明〕同朋友在网上讨论的整理。之前整理方含和伊群的“巴黎公社诗”那段公案(方含│依群│纪念巴黎公社()),想到一个问题。文革早期运动结束以后,感到“不甘”或“幻灭”并开始“异议思想”之路的主要是两拨人,一拨是干部子弟(如方含和伊群),一拨是旧上层阶级子弟(如北岛)。有机会弄到灰皮书黄皮书以及其他禁书的,主要就是这两拨人。他们的后来的“异议”或反抗,几乎没有向左的。《中国“文革”时期民间异议思想文献选辑(-)》,基本就是这两拨人言论。事实上是他们主导了后来的“思想启蒙”。 说是“民间”,但宣扬“血统论”的是高干子弟,反对“血统论”的是“出身不好”的家庭子弟,也就是旧上层(至少是中层以上)阶级家庭的子弟。 平民或贫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比如梁晓声,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是汇入“伤痕文学”之类的潮流里。 波兰复辟后,瓦文萨之流把波兰工运勾画成一场自觉向资本主义“回归”的运动。一个波共时期坐牢的团结工会左翼分子答道:“如果是为了资本主义,我一天的牢也不会愿意坐”。〔注:记忆有误,原话是“我可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去坐哪怕一个礼拜或一个月的牢,更别说八年半了!”〕当年的中国,没有这种比较自觉的左翼分子。即使嘴上能说类似的话,意识层面能这样想,但实际上还是差很远。 王安忆关于与陈映真交往文章,也是明显例子。这些后半代的知识分子,跟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斗争,在心理上是极其隔膜的。 老辈人出国后左转的有几个?我所知道的,最明显左转的是北岛,去年他写过一首挺长的诗,写工人,我读得满感动。诗人中极少见了。他的《时间的玫瑰》一书很注意勾划那些大牌诗人的政治态度,他有很多文章都在了解和探讨历史上以及许多国家里的革命,虽然他对多数结局感到失望,而且时不时地要退回到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堡垒中喘口气,但确实表现得非常认真,是一种试图寻求精神出路的态度。
北岛是金融界精英的后代,读北京四中的时候被高干子弟同学打击,语言上打击吧。所以后来他会写献给遇罗克的诗,《回答》、《结局或开始》,两首都写得很好。我一直认为《结局或开始》是北岛最好的诗。 毛时代相当多数知识分子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不管是高干子弟,还是旧精英的后代。 方方也做过工人,还写过表扬底层劳动者的文章。只要劳动者好好干活,对她们没有威胁,没有冒犯她们,不会引起她们不快,方方们是乐于表扬表扬劳动群众的。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jt/5912.html
- 上一篇文章: 所谓仲裁,不过废纸一张
- 下一篇文章: 旅游攻略古港之旅,愿你所遇都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