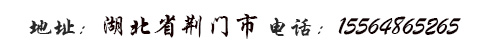朴槿惠昂山素季们来了,世界由女人主宰会变
|
沈阳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5212240.html 老Z|文 这个世界若由女人主宰战场将变成孩子们嬉戏的广场枪炮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鲜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位诗人写下上面几句话。显然,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看来,男人,是引发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把这个世界弄得越来越糟。顺理成章的逻辑自然是,既然男人指望不上,不妨寄希望于女人。 他对男人的绝望情绪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一时忘了这样一个事实:从14世纪开始,欧洲出现多位女性君主,例如丹麦的玛格丽特一世(~年在位),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年在位)与维多利亚女王(~年在位),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一世(~年在位),以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年在位)等,而且,无论哪一位,都是货真价实的铁腕人物。在政治游戏中,“铁腕”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叶卡捷琳娜二世(-年在位)上台后不久,就制定并启动了入侵波兰和土耳其的计划 无论如何,一战后的发展趋势,倒是符合这位欧洲诗人的期待。17世纪已有萌芽的女权运动,经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至年代前后,主要是反抗政治上的性别歧视,主要焦点是争取普选权;第二次是~年代前后,主要是反抗经济上的性别歧视,主要焦点是争取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同工同酬),到现在似乎收获颇丰。 年,美国华盛顿,一千多名来自各州的女性,在街头为争取女性选举权示威游行 只不过,说到经济上的成果,我们只能跟着感觉走,姑且信之: 女人兜里到底有多少钱——这是体现女人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外人一般都不太清楚,据说从购买力——一个混沌不明的指标——上讲,可能是男人的1.5倍以上,至于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统计学问题,甚至同时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至于就业上的性别歧视及其程度,由于有些行业天生具有性别倾向,分析家们也很难进行精确的、综合的量化,因而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所以敢跟着感觉走,说到底是因为经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感觉。 比较之下,要判断政治上的成果,我们不得不依靠一些数据,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政治生活有些过于遥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数据看上去比经济数据更易获得,也更为可信:算一算女性政治家的数量及其增减趋势似乎就可以了。 在最高级别政治家层面,女人的攻势屡屡获得重大突破。年,第一位女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登上欧洲的政治舞台。由于英国历史上出现过至少六位伟大的女性君主(包括以已经在位63年的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突破首先在英国发生并不太令人感到惊讶。 撒切尔夫人(-年),英国第49任英国首相(-年在任),至今为止英国唯一一位女首相,也是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 不过,到了年,当朴槿惠——东亚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入主青瓦台时,男权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震惊,女权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雀跃了,因为韩国有着很长时间的男尊女卑传统,尽管它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多位把持国政于一时的皇后与太后。 在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缅甸传奇女子、美貌与智慧兼备的昂山素季卷土重来,领导全国民主联盟赢得联邦议会的选举,获得单独组成新政府权力。 昂山素季(-),缅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年带领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的胜利,但选举结果被军政府作废,之后被军政府软禁15年。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到了年,美国,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或将迎来它的第一位女总统。 11月24日,希拉里赢得北美劳工国际工会(LIUNA)支持,在党内提名角逐中的优势进一步强化。 说到美国,不妨再看看女人在国会层面的突破。美国国会研究局(CRS)提供的数据是,自珍妮特·兰金于年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议员以来,美国国会一共出现名女议员;而目前这届国会(第届)共有女性议员位,其中,众议员88位,参议员20位,占比都在20%左右。 有趣的是,根据各国议会联盟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发布的《年女性参政地图》(WomeninPolitics:),在政治事务上备受美国批评的非洲国家卢旺达,女议员占比竟然达到63.8%,稳居世界第一;美国排在第83位,中国(女性人大代表占比23.4%)排在第61位。这份报告同时显示,在中央政府层面,女性部长占比一项上,同样在政治事务上备受美国指责的非洲国家尼加拉瓜以57.1%的成绩居首,美国以31.8%的成绩排在第23位,中国以8.3%的成绩排在第77位。 罗丝·穆甘塔巴娜(RoseMukantabana,-),卢旺达前众议长(~年) 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女性政治家占比高与国民的幸福指数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让我们先看看丹麦、瑞典、挪威——幸福指数最高的前三位国家——的情况。女性议员及女性部长占比指标上,丹麦分别是39.1%、45.5%,(分别排在第15名和第7名),挪威分别是39.6%、47.1%(分别排在第13名和第5名),瑞士分别是31%、42.9%(分别排在第34名和第9名)。 再看看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幸福指数最低的三位国家——的情况。女性议员及女性部长占比指标上,多哥分别是16.5%、21.4%,(分别排在第88名和第41名),贝宁分别是8.4%、22.2%(分别排在第名和第39位)。中非共和国则因为没有议会,以及无法获得政府部门的信息,在报告上没有相关数据。 从上面这两组数据看,女性政治家占比与幸福指数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考虑到女议员占比稳居世界第一的卢旺达幸福指数排名倒数第5的现实(女性部长占比居世界第一的尼加拉瓜幸福指数排在第65位),又让人不敢轻易相信这个结论。确实,影响结论的因素实在太多,例如,一国的人口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历史及文化因素更能影响政治家的性别比,至于幸福指数的可参考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幸福”定义的量化方法,以及等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调查过程。 不过,正如蔡东杰在《政治是什么?》一书中所讲,政治是一种响应社会需求的治理活动。因此,在回答“女性政治家是否比男性政治家更能给国民带来幸福”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搞清楚当下的社会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以至于使得前面那个问题看上去像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简化为两种: 一种是性别无法影响结果的问题,例如需要靠制度来解决的基本问题(例如生存、平等与自由),以及需要靠技术来解决的问题(例如CPU速度的提升),以及需要用宗教、文化等手段来解决的问题等; 一种是性别会影响到结果的问题。这个问题无需举例,因为只要相信男女有别、各有天赋,就必须承认一定存在这些问题,在其中某些问题上,女性处理得好的概率一定比男性高。 因此,在“女性政治家是否比男性政治家更能给国民带来幸福”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因为长期以来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一事实出于某种心理机制而做出肯定答复,也不能因为我们是技术主义者而做出否定的答复。 其实,即便是一些看上去“性别无法影响结果的问题”,既然男性政治家迟迟交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卷,那么,在智商、情商相近的前提下,为何不多给女性政治家一些机会呢?或许正如梅兰·维尔维勒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最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女性的参与是根本解决不了的。我是说真的,哥们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jd/5051.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度回顾年10大女性时刻盘点
- 下一篇文章: 正式下发4月开始重启封村封小区政策,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