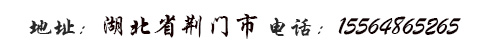蔡崇达皮囊之残疾一位高傲坚毅的残
|
导语:昨天给大家分享了《皮囊》书中第二部作品《母亲的房子》,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书中第三部作品《残疾》。 《残疾》是作者对他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的回忆。俗话说母亲是家里的温度,父亲是家里最厚重的墙,我想父亲的形象在我们大多数心中来说都是高大威猛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温存的庇护港。 所以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除了心疼书中那个高傲又坚毅的父亲,就是感动,当然也学会了珍惜。 李敬泽先生在序言中说到:“自70后起,在文学书写中,父亲就失踪了,不是去了远方就是面目模糊,他不再是被尊敬、畏惧、审视、反抗的对象,他直接被屏蔽,被搁置在一团模糊的阴影里。而在蔡崇达这里,父亲出现了,被反复地、百感交集地写,这个父亲,他离家、归来,他病了,他挣扎着,全力争取尊严,然后失败,退生为孩童,最后离去。” 开头作者就以中风出院的父亲晚上10点回到家,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他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他父亲的之类话,但他父亲的舌头瘫了一半,却依旧激动含糊地对抱着哭的人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说完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然后大家跟着笑了。 他父亲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看上去像是不错的开始。但是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他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 读到此处可能大家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明知等欢闹褪去,终究逃不过残酷的现实,但他父亲依旧在亲戚朋友面前逞着强,一副无所谓,云淡风清笑着的皮囊,皮囊内心深处的是他父亲那高傲了一辈子内心最后的一点倔强。 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内心的心酸以及对父亲的心疼,从这一刻,他再也找不到那个顶天立地的父亲了。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医院回来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严重,一直以为过段时间他还可以意气风发地站起来,以为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之前一样,还会是之前那个威严不可犯的一家之主,但其实那是再也不可能的事情,作者不忍心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告诉他。 直到第二天他摔倒了,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然后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使命的不让眼泪落下来。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作者也不习惯看他哭。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他也死命的出力,很想配合自己的儿子站起来,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最后,他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他笑,但爬到他父亲脸上的滋味太多了,最后扭曲成连作者都描述不清的面部表情。 面对这个结果在他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 只是为了减少疾病压在他父亲身上的重量,康复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想给他父亲以后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希望。但是时间长了,大家都没耐心了“演了”,最终戳破这张纸的就是他父亲。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但他父亲心态很快就调整回来了,他觉得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只要他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他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他一家人都乐于享受他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我想他父亲也害怕自己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他不想成为整个家的累赘,他害怕的同时又很脆弱,或许人活着总希望能找个能看见希望的出口吧,尽管这是假的,但谁也不想破坏这份美好。 为了配合他父亲,营造会康复的假象,全家人陪着父亲进行康复训练,全家人都活在这虚幻的快乐之中,直到闽南的台风打碎了这一切。 虽然知道根本不是台风的错。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至今仍愿意诅咒那次台风。 台风在于我从来没有悲伤的色彩,直到那一年。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某些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趾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姐姐喜欢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肉,血流了出来,姐姐吓得到处找药布包扎,他依然没有感觉地沉沉睡着。只是醒来的时候,看到脚上莫名其妙的纱布,才傻傻地盯着发呆。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 他父亲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闽南秋日的第一场特大台风,霎时铺天盖地到达了这座小镇。 他父亲在台风天执意要出门锻炼,面对家人的阻挠,争执、脾气开始变得非常暴躁甚至怒骂“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操起拐杖对着家人一顿乱挥,只是因为难以疏解内心对如此命运的不甘与不解,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以及难以放下最后的那点尊严。 读到此处,我内心很触动,其实他父亲可能一直就隐约猜得到结局,但是他无法妥协,总觉得还会有希望,那怕只有一点,那也是希望啊。 人啊,最可怕就是内心还有不该有希望,当希望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时候,才是最伤人的,但他没办法,他内心太煎熬了,太难受了,难受的想无时无刻发泄。 最后他父亲妥协了,妥协后的父亲再也不是父亲的形象了,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他开始变得不再坚强,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孩。 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父亲讲话时刻把死挂在嘴边,讲话也像是在讲遗言一样,作者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作者。 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作者气到对他父亲发脾气。细腻的笔触描写出来的内容太真实了,因为长大后的我,最害怕听到死这个字,仿佛这个字一说出口就会有某种魔力一样会失去,对于失去,我们实在太害怕了。 他父亲在快要死的时候,又开始惧怕死亡,舍不得。但最终他父亲还是去世了,但他知道他父亲尽力了。整部作品最后以父亲去世后给他和他母亲托了个梦为结尾。 作者父亲受尽皮囊的折磨,但又有着倔强顽强的性格,使得他拼尽自己全力,成了与皮囊作对抗一类人的缩影。生命本轻盈,却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便要时刻记着肉体是拿来用的,而非拿来伺候的。 这部作品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形象,他高大威猛,顶天立地,但他也会脆弱和害怕。其实生活中大部分父亲都一样,顽强又脆弱,只是他们总是在我们和外人面前,表现的无坚不摧去维护他父亲的形象,实在迫不得已才会露出脆弱面容。 我只希望我们的父亲可以在遇到困难事情的时候不要那么坚强,不要一个人硬扛,因为我们可以,我们也愿意和你一起分担。 如果对《皮囊》书中其他章节感兴趣的话,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会不定期更新分享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ly/9614.html
- 上一篇文章: 漳州情杀案内情疑曝光女方多次出轨被抓包,
- 下一篇文章: 发动机前置中置后置布局都有啥特点,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