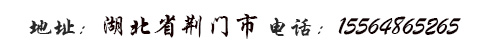思南文学选刊03目录
|
白癜风可以抹药吗 http://disease.39.net/yldt/bjzkbdfyy/6149570.html 《思南文学选刊》 SiNanLiteraryJournal 年第3期 目 录 叙 事 葛 亮瓦猫 潘向黎荷花姜 张玲玲夜樱 南 翔苦槠豆腐 张 者山前该有一棵树 王方晨凤栖梧 诗 歌 李松山世界卡在词语的间歇里 帕特里克·雷恩禤园阿九译树叶包含在它的生长中 随笔 葛兆光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 许 宏二里头都邑“不动产”的大发现 边界 康 赫无尽的写作 莫里斯·迪克斯坦方晓光译鲍勃·迪伦与摇滚乐时代 重 温 马塞尔·埃梅李玉民译穿墙记 资 讯 btr它也是收音机、车轮、书籍 思南文学选刊掠影 点击上方图片进入年第3期购买页面 叙事·葛亮《瓦猫》 选自《当代》年第1期 叙事·潘向黎《荷花姜》 选自《人民文学》年第5期 叙事·张玲玲《夜樱》 选自《小说界》年第1期 叙事·南翔《苦槠豆腐》 选自《长江文艺》年第5期 叙事·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 选自《收获》年第3期 叙事·王方晨《凤栖梧》 选自《北京文学》年第5期 诗歌·李松山《世界卡在词语的间歇里》 选自《羊群放牧者》,长江文艺出版社,年11月版 诗歌·帕特里克·雷恩《树叶包含在它的生长中》(禤园、阿九译) 选自《雷恩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月版 随笔·葛兆光《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选自《读书》年第5期 随笔·许宏《二里头都邑“不动产”的大发现》 选自《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山西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 边界·康赫《无尽的写作》选自《黑暗中的光体——影像写作与局部影像史》,作家出版社,年1月版 边界·莫里斯·迪克斯坦《鲍勃·迪伦与摇滚乐时代》(方晓光译) 选自《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读库 新星出版社,年6月版, 重温·马塞尔·埃梅《穿墙记》(李玉民译)选自《我会在六月六十日回来:埃梅短篇小说全集》,乐府文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6月版 资讯·btr《它也是收音机、车轮、书籍》思南文学选刊概览 《思南文学选刊》年第3期已出版,本文为评论家丛治辰对《思南文学选刊》年第3期的阅读印象。 点击上方图片进入年第3期购买页面 关于“穿墙术” 《思南文学选刊》年第3期概览 文/丛治辰 本期《思南文学选刊》的“重温”栏目刊发了马塞尔?埃梅的《穿墙记》。感谢这一选择,使我有机会再次领略这篇小说灵动轻逸的叙述之美。小说开宗明义地告知读者,马蒂耶尔是一个异人。但他其实和我们很多人一样,住小房子,当小职员,老实巴交地上班和回家,近于机械呆板。突然有一天,世界在他面前裂开一道豁口,他发现自己凭空多了一身穿墙而过的本领。和很多安分守己的四十三岁男人一样,马蒂耶尔对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不感兴趣,甚至相当不适。他顽固地抗拒这一改变,直到新来的领导逼迫他做出更无法接受的改变——改变他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行文习惯。或许就在那一刻他才赫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信仰的庸常而稳定的生活其实远没有那么牢靠。我猜想他当时的愤怒并非只是针对那位领导,而是出于一种被背叛与被欺骗的强烈痛苦。在此之前,穿墙术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对“墙”这东西司空见惯,觉得再自然不过,即便被安排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也可以安之若素。但如今他终于发现,生活的真面目便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因此当他从墙后伸出脑袋,其目的就并非仅仅是戏弄那位领导,而是要向包括这领导在内的世间一切的“墙”发出嘲笑。在笑声里那些墙纷纷坍塌,世界正式向他敞开。当他游戏般出入银行和监狱,小说变得多么快乐。我以为这里面没有什么“杀富济贫”的意思,毕竟那些奉他为英雄的人们,并没有拿到半枚金币。人民热爱的不是金钱,而是穿墙这一行为本身,马蒂耶尔的异能让他们平庸生活的沉闷一扫而空。 当然,他总会遇到那个金发女郎的。其实无需作者暗示,我已经在隐隐担忧他的结局,当那女郎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马蒂耶尔无可阻挡的自由生活结束了。这种预感让我困惑良久:那种凉丝丝的危机感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说,他之所以丧失自由是因为不应有的欲望,因为觊觎那本不属于他的玫瑰,那么何以此前他江洋大盗的行径,却让我们那么兴奋,而且轻松?我想唯一的解释大概是:那些金钱在马蒂耶尔这里本来就没有重量。除了给自己预备那栋并不起眼的安全屋,马蒂耶尔对挥霍钱财似乎并无兴趣。正因为此,他的偷盗行为和从墙里伸出脑袋一样,只是一种嘲弄,因此这一行为是向全世界——包括书中的人们和书外的我们——敞开的,是那么坦荡明亮。但这位金发女郎,马蒂耶尔却无法与世界共享。这一行为由真实的欲望驱动,而不再出于快乐的动机,这让它成为一个可耻的阴谋。在穿过这女郎的房屋和院墙时,马蒂耶尔失去了遁出监狱的从容,盖因这一次他并非为了自由穿墙逃脱,而是将世界挡在墙外,真正过上了囚徒生活。马蒂耶尔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筑起一堵墙,他的肉身因此变得沉重,终于锁在墙心,成为冷硬墙体的一部分。 马蒂耶尔的悲惨际遇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的告诫:“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轻逸》)卡尔维诺借用《十日谈》里的一幕来说明“轻逸”的文学真谛: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诗人卡尔康蒂轻盈地一跃,溜之大吉,将企图戏弄他的那些纨绔子弟留在墓地当中。在我看来,马蒂耶尔的英雄行为、他显赫一时的名声和令人感伤的下场,同样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更加醒目地警示我们,轻举妄动是如何葬送了自由而轻逸的小说精神。和这期刊物中的其他作品参详对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这篇小说绝不仅仅是一则妙趣横生的现代传奇,而根本就是有关小说艺术自身的一则寓言——关于小说的形式、内容、主题,乃至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美学原则。在此意义上,在本期刊发的几乎每篇作品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点《穿墙记》的影子。 就像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它最核心的情节——把胜利渠边的胡杨树挪到荒苦的矿山——不就是一种穿墙术?重点当然不在于那棵树穿越空间的距离,而是借由这样一棵树,以及胡老师对树的讲述,那些生活在矿山的孩子们与绿洲、与绿洲以外更加广阔的世界之间那堵“墙”被凿开了,绿色与甜水奔涌而来。一棵挪不活的胡杨树,其意义几近于幻觉,但幻觉是可以撬动现实的,它让那些孩子们有了走向远方的可能。而且,树是幻觉,人呢?张者以一种朴素的修辞手法,将那位走了霉运的胡老师与死而不倒、永存于孩子们记忆之中的胡杨树联系在一起,在一种万物有灵的氛围里胡老师跃出了他的皮囊,弥散到无穷广大,提供了小说结尾处浓郁的抒情。而历史也因此得以卸下单调而沉重的面具,露出它丰富的表情。 葛亮《瓦猫》之动人,同样发生在穿墙而过的时刻。那些在香格里拉和昆明神秘出没的瓦猫,就像是马蒂耶尔从墙后探出的脑袋,引诱着“我”和所有读者,去剥开被厚重墙体掩盖的秘密。关于西南联大和那个时代,已经讲述得太多,那么多人生,那么多故事,层层叠叠,令人窒息。而葛亮的出色之处恰在于,能够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时代一路穿行,逼近那所昙花一现的辉煌学府,召唤陈旧的记忆一点点醒来;但是又突然推远,在更加绵长开阔的时空结构里,制造出一种令人惘然的美感。但让我感到费解的是:那个叙述者“我”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深意?如果他只是一个带领读者不断穿过历史迷雾与深沉人心的异人,那么他应该像显赫时代的马蒂耶尔那样轻盈。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叙述者,他对自己喋喋不休地讲了太多。这让他本人变成了马蒂耶尔的金发女郎,多少拖累了他穿墙而过的敏捷步伐。 和暧昧曲折的《瓦猫》相比,潘向黎《荷花姜》的意图似乎明白无误。小说一开始,在叙述者和那对男女之间就有一道墙,这道墙的厚度与透明度都非常理想,天然适于穿越。这有赖于丁吾雍的分寸感:为了挽留这对富有魅力的客人,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和他们保持距离。窥探,但并不介入。小说中年轻女子那么神采飞扬又那么楚楚动人,大半是因为这样合适的距离,或者说,小说家那精妙的穿墙技艺。因此,当丁吾雍逐渐按捺不住想要接近这位年轻女子的时候,我再次感到无比紧张,和马蒂耶尔遭遇金发女郎时一样:不!停下来!好在,女子那句凶险而难辨真伪的谎言,让她“咻”的一声穿墙而去,逃脱了叙述者的抓捕。读到那句话时的快意,可以与《百年孤独》里俏姑娘被床单带走的那一刻相比。然而那个男人居然再一次出现了,这简直让我疑心自己已经听到了马蒂耶尔那笨重的呼吸声。当那个男人和他的前妻躲进小包间里窃窃私语,我忍不住要把门外逡巡窥伺的丁吾雍直接拉走:这样就很好,不要再做些什么了。是的,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自己猜。——我多么希望那个男人没有孤独到和丁吾雍说那么交心的话呀,和最初出场时那个沉稳男子相比,他的表达欲似乎太多了一些。 马蒂耶尔式的快意不仅存在于小说当中。葛兆光《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是为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撰写的学术书评。与宫崎市定《科举史》、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相比,艾尔曼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跳出制度史和社会史的既有视角,揭示了科举制度与明清政治生态、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没有将科举考试孤立地理解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而拆除掉隔绝不同研究领域的那些人为的意识障碍,让他的研究对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葛兆光与艾尔曼的辩论同样精彩:他完全理解艾尔曼的意思,但是各自不同的立场并没有造成对立,而成为沟通的前提。事实上,学术思考的魅力,不正在于不断拆除既有认识所造成的思维局限吗?在此意义上,许宏的《二里头都邑“不动产”的大发现》简直像是一个精心构造的隐喻。一方面,他老早就以“大都无城”的观点,反复和“无邑不城”的传统看法争辩:忘记你们在想象中垒起的城墙吧,只有拆掉它们才能明白二里头都邑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其实依然是以“墙”作为线索去进行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宫殿区道路网的发现,已足够证明这座都邑显然出自复杂的人为规划。而道路是什么?它也是一种墙,却不仅能分割,还能联通。就像后来发掘的宫殿区防御设施一样,曾经它用以隔绝,而今却成为追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条通道。但许宏这则考古纪事所提供的快感还并不仅限于智性层面,在文章中,他多次提到考古挖掘工作因延伸到现存村庄民房而不得不中止,字里行间不无遗憾。但我很想说:不,那并不是阻碍。恰恰在这相遇当中,几千年的时光被击穿了,古老中国与今日中国交织在一起,撞击出一种如青铜器般钝重的美感。 所以,《穿墙记》岂止是有关小说的寓言,它是一切书写的寓言,也因此是一切思考的寓言。思考与书写的价值,正在于轻快地跃过沉重、呆板、单调、压抑的世界表象和既有知识,在发现与创造当中获得自由,感到狂喜。当然,轻有其价值,重或许也有其价值。但是如果根本不曾意识到墙的存在,或意识到了墙的存在,却困于其中无法逃脱,又或者刻意制造“鬼打墙”,就或许失之于粗疏、脆弱与油滑。就此而言,关于文学中的穿墙术,其意识、技术与实绩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视为这一期《思南文学选刊》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呢? 思南文学选刊资讯 点击上方图片进入年第3期购买页面 它也是收音机、车轮、书籍//// 文/btr 第24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启动 据5月10日“澎湃新闻”报道,第24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启动。今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由网易LOFTER冠名,这是新概念作文大赛首次得到网络平台的冠名和支持。自4月30日至6月10日,平台将上线“文手春令营”创作接力赛,由《萌芽》给出创作主题,每两周更新一次,用户根据主题进行限时创作,每期创作将评选出1-3篇优质作品。该活动将由知名青年作家王若虚,《萌芽》人气作者负二、不日远游,以及《萌芽》编辑七月人担任点评嘉宾。年诺贝尔文学奖揭秘 5月10日,瑞典学院公布了按规定尘封50年的年诺贝尔文学奖审议档案,当年的得主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据悉,索尔仁尼琴几乎是当年评委们的一致选择,只有阿图尔?伦德奎斯特强烈反对。而他击败的另两位进入决选名单的作家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及澳大利亚小说家和剧作家帕特里克?怀特,两人后来分别获得年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我想通过技术来谈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现旅居柏林的阿根廷青年小说家萨曼塔?施维伯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眼睛》(Kentukis)英译本近日出版。同时,根据她的小说处女作《营救距离》改编的电影也将于10月由网飞推出。以下采访节译自4月24日出版的《卫报》—— 谈疫情中的一年:疫情的头几个月,我被困在阿根廷——我很恼火,但那三个月对我来说是好事,可以坐下来,调整自己的节奏,与工作重新连接。但开始时很难,因为从一天到另一天,关于什么是虚构、什么不是虚构的想法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变化。在第10天还是第15天,我记得看见电视上的人们拥抱他们的朋友,心想,“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小说有如此强烈的红线来划分:这是以前,这是以后。从那条红线出发进行写作是非常困难的。 谈《小眼睛》里的科技设备:作为一个读者,我有一种感觉,文学和科技之间出了问题。我读过的每个作者,甚至我自己,我们一直在付出巨大努力不说出技术之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接受了技术,但在小说中,我们试图不去谈论它。我想通过技术来谈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然后出现了“小眼睛”(Kentuki)的想法——它是WhatsApp、推特、脸书和手机之间的混合。它是一切,所以我不需要命名任何东西。 谈科技的善与恶:我们已经开始认为科技是个坏东西,但我认为它是中性的。科技不仅是电脑和WIFI:它也是收音机、车轮、书籍。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更多取决于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小眼睛”是一个麦高芬:我想写的是非常人性化的人物,他们做的正是读者在相同情况下会做的事,然后突然向他们展示,这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谈《营救距离》的电影改编:一开始我很担心,因为小说中最强烈的东西,是叙事正在欺骗你的那种灰暗感觉。但画外音在电影中可能是危险的:它可能无聊,观众有时没能专心听。所以写剧本是一个挑战。但我已经看到改编的结果,我对它非常非常满意。 《格兰塔》揭晓最佳西语青年小说家(第二辑) 第期《格兰塔》(年春季号)刊出最佳西语青年小说家(第二辑)。由萨尔瓦多小说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阿根廷小说家罗德里戈?弗雷桑、诗人及西语《格兰塔》联合创始人奥雷里奥?梅杰等六人组成的评委会从68人的初选名单中最终选出了25位35岁以下西语青年小说家。 评委之一、西语文学出版人瓦莱丽?迈尔斯在前言中写道,“这批西语青年小说家的突出特点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虽然是从同一种语言里生长出来的,却来自23个不同国族,更有无穷的地方性变化——地区、城镇、村庄;这种单一的语言因为传统、历史、种族、宗教、地理各不相同而具有无穷的分叉。”她继而举例,“‘青豆’这个词是很好的例子:在西班牙,青豆是judíasverdes,在墨西哥是ejotes,在阿根廷是chauchas,在智利是porotosverdes,在秘鲁是vainitas,在哥伦比亚是habichuelas。纳博科夫喜欢把俄语元音等同于橙子,把英语元音等同于柠檬,而我想西语元音是不是更像石榴中的红色果核群。若按每秒钟说出的音节计算,西班牙语是世界上第二快的语言,仅次于日语,这一点阿莫多瓦的粉丝应该不奇怪。西语最长单词hipopotomonstrosesquipedaliofobia意思是‘对长单词的恐惧’。怎能不崇拜一种能产生这种东西的语言呢?一种拥有美丽词汇的语言,比如nefelibata,来自古希腊语的nephélē‘云’,和bátēs‘步行者’,这个词是由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创造的,并得到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响应。‘起来,起来,云步行者要当心,你的脚也可能会被云困住。’” 英语是欺负人的“后妈” 裘帕?拉希莉10年前与家人搬到罗马。她放弃了所有英语阅读,开始只写意大利语。年,她出版了用意大利语写的第一部小说Dovemitrovo——直译为《我在哪里找到自己》或《我在哪里》——如今由她自己翻译成英文,书名为《下落》。 小说讲述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在一年时间里在一个不知名城市里漫游的故事,每一章都是一份浓缩的遗憾和孤独。第二章《在街上》,叙事者撞见一个男人,一位朋友的丈夫,她“可能与他有过关系,也许共同生活过”:他们走进一间内衣店,因为她需要买一双连裤袜,这让读者以为已经开始了一个特别的故事。但这些街道大多数都不知通向哪里。这些章节讲述了不同的关系或联系:探访母亲;与咖啡师的日常聊天;一次转瞬即逝的相遇。 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裘帕?拉希莉说:这是一本关于归属和没有归属、地点和流离失所的书。她认为这是“一个女人在某种城市孤独中的肖像”。虽然《下落》是一部小说,但它几乎可以被描述为彼此关联的短篇小说集,因此至少在形式上,拉希莉处于她熟悉的领域。她可能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但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什么比采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更大胆的实验呢?就像21世纪的亨利?詹姆斯式女主人公,她避开美国,而选择了罗马旧世界的魅力。她说:“真的很难解释生活中那些驱使你朝人、地方、语言而去的力量。对我来说,抵达一种语言,然后到达一个地方,随后抵达新的生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存在方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早在去罗马之前,她就一直觉得自己存在于“一种语言上的流放”中。她出生在伦敦,是印度移民的女儿,两岁时全家搬到美国。她在罗德岛长大,经常去加尔各答,她觉得她的故事比她学校的朋友们写的故事“复杂得多”。“总是有‘另一个地方’‘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世界’”。她四岁前一直讲孟加拉语,这既是她的母语,也是“一种外语”,因为她不会读也不会写:这是她父母的语言,“他们世界的语言”。拉希里和她妹妹接受的是英语教育,她渐渐认为,英语是一个欺负人的“后妈”。“我为什么要逃?什么在追我?谁想限制我?”她在《另一种语言》里问道。“最明显的答案是英语这种语言。” 编剧和导演是小偷 以下文字节译自泰国导演及艺术家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的展览《我常给你写信》—— 编剧和导演是小偷。我们秘密偷取看到和遇到的真相,并将其重构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偷偷写一些也许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但我们在剧本中把它们变成现实。我们秘密要求工作人员建造类似于我们记忆中的场景(或很多时候,我们简单复制真实地点)。如果有些事实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我们就会修改或扭曲它们,并把它们作为现实重新讲述。 我们有自己版本的现实。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版本。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多了解我们的朋友,他们其实是我们所定义或书写的人。当我看到你时,我有我的版本的“你是谁”。同样地,你也有你的版本的“我是谁”。我甚至还有我自己版本的、你可能会不同意的“我”。 写作、创造和想象是编剧和导演的基本天性。如果你一连拍了5到10年的电影,你会在电影中做梦。你会把陌生人看成角色,把周围环境看成镜头。 思南文学选刊 主管/主办:上海市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 社长/主编:孙甘露 副主编:黄德海、方岩 特约编辑:项静、张定浩、木叶、btr 封面设计:谢翔 版式制作:兰伟琴 目录英译:朱绩崧 广告发行:李晓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ly/7058.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新快讯甘孜州头号黑老大被逮捕,刷新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