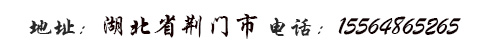号山丘
|
塞尔西奥·拉米雷斯·梅尔卡多(SergioRamírezMercado) 致亨利·鲁伊兹(莫德斯托) 西班牙语“manjol”这个词从英语“manhole”来,是指进入下水道系统那个洞。井盖丢了会让没留意的司机造成严重事故,行人就更麻烦,尤其如果晚上在马路中间溜达。这类事故最近在尼加拉瓜越来越频繁,因为国际市场上制造井盖的金属价格飙升——铁、黄铜、青铜等等,导致这些设施经常被贼盯上。 比如黄铜的价格吧,五年里翻了三倍,已经达到每吨美元,铅也到了每吨美元的历史价格,跟青铜差不多了。这主要是有些国家,像中国和印度,在工业和基础设施上加大了投资,消耗非常惊人。 这种现象鼓动马那瓜的铸造厂收购偷来的金属材料不问出处,于是不光井盖,包括电线、电话线、传送电视和网络信号的同轴电缆、光纤,连同自来水表和消防栓都纷纷消失;教堂圣物、墓地栏杆和装饰也不能幸免,哪怕名人呢,就像贝纳尔多·奥希金斯将军的青铜半身像,也得多亏警察某天早晨追捕小偷查抄回来——那帮人把他从美洲名人大道的某处底座上起开、用手推车运走,打算卖给一家废铁加工厂熔掉。 (另外一种需求很大的金属是铝,又轻、延展性和强度又好,广泛运用在一次性包装尤其饮料罐上,而且还能回收。捡这种废包装没有什么法律风险,一般在住宅区的垃圾箱,还有餐馆、酒店、迪厅和食堂就能收很多。) 写前面那些是在找办法开始这个故事,结果好像有点跑题了;我在文学写作班里提醒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短篇,选好中心事件就直奔主题,所谓斗牛先找角。 虽然都这样了,仔细想想,井盖和罐子的问题还是给了两种开篇的可能性,暂且叫做A和B吧: 可能性A,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踩两只旧军靴,某周三早上8点来钟跟儿子一起推着小车,走在马那瓜南城住宅区圣多明各高地金合欢树葱郁的街道上。孩子12岁左右。该男子的工作是在孩子的配合下翻垃圾箱、找扔掉的啤酒和饮料罐,除了垃圾箱里的东西,他什么都不在意。是个星期三,因为市政垃圾车那天在那个区清理,各家的垃圾箱都早早摆到人行道旁边。他俩都尽可能不出声,免得引起女仆们注意,她们一般不喜欢有人来翻垃圾,弄得到处都是。 巧的是,那天早上,其中一座宅子的后勤出入口,一位穿天蓝色制服、白色围裙的女仆正跟骑摩托车的快递员签收电费单,扭脸看见了老少两人。她很年轻,长得不错,刚洗了澡,黑色的头发闪着水光。她认识他们,以前因为翻乱垃圾的事跟推车那男的争过几句,所以他打算直接抄过去;意外的是,她叫住了他,说里面有好多罐子,都可以给他拿走。 我们就当这是种心血来潮的慷慨吧,确实头天晚上办了生日会、来了无数的人。这是笔好买卖,她少个差事,因为轮到她收拾,得把罐子挨个儿扔到黑塑料袋里拿路边去;他也捡个宝贝,这相当于整整一早上的收获了,幸亏赶在垃圾车之前,不然就被带出高地区、朝圣多明各岗和观景台去了。 就这样,那名男子和他儿子由女仆领头从后勤口进了院,有点畏手畏脚的,沿着一条石板路——路铺在修剪过的草坪上,旁边是一排结满果子的矮椰树,护卫着绿松石色的游泳池——直走到头天晚上设吧台的角落里;去掉桌布裸着的折叠金属长桌还在,挨着几个装满出租玻璃杯的筐,还有两个巨大的用来冰镇饮料的锌桶,里面冰已经完全化了,水里游着几听还没来得及打开的饮料。一堵爬满三角梅的墙边是空罐子坟堆,酒保随手扔出来的,有些还被捏扁了。 女仆消失了一阵,拿回一捆大号的黑塑料袋,他们立刻抖开装了起来。酒瓶子也不少,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龙舌兰酒,不过已经解释过了,那男的除了铝包装别的都没兴趣,所以把玻璃瓶都撂在了一边,尽管好几次被催“一块儿”。总共装了五大包,搁回小车第一趟他拿了两个,孩子拿了一个。 蓝绿色的游泳池附近有个开敞的亭子,蜿蜒的小路有一段拐过去离得很近。亭子地面是上了釉的泥砖,在早晨明亮的太阳下反光;一副蕉麻吊床,挂在嵌进亭柱的两个圆环里;一张玻璃面铁桌,围着几把铁艺座椅。 总是走在前面给他们开路的女孩是第一个吃惊的,突然发现主人也在亭子里,穿着睡衣,坐着轮椅,腿上摊着早上的报纸。可能之前就在那儿,只是去找罐子的时候三个人谁也没注意。他的生日会结束得很晚,将近凌晨4点,她以为他还睡着呢。轮椅后面站着一个护士,一身板正硬挺的白制服,扣子直扣到脖颈。 手提两个黑塑料袋的男人也注意到轮椅里的人了,一种本能让他站住、也确实站住了,就孩子还往前走。男人的眼睛没有停留在对方脸上,而是发现他少了一条腿,从膝盖的位置截断,睡裤在那个地方被仔细折起来挽了个结,用别针别住。 他染过发红的头发已经稀疏了,眼睛下面的皮肤松成两个塌塌的眼袋;脸色很差,慢性糖尿病人那种颜色;远远就能闻到“三冠”牌古龙水泡柑橘花那种甜腻忧郁的气味,估计是护士洗澡之后给他抹的,背上、胸口、脖子,有毛的地方。 独腿人先是笃定地看着那个男的,带点嘲弄地打量他,接着微笑起来,脸上露出愉快的惊喜。男人没说话,松开袋子,就像偷东西被抓了个正着;身后的孩子倒是好好保管着一直拽在肩上的塑料袋。 可能性B,圣多明各高地同一个住宅区,不过是清早、太阳还没出来,落满金合欢花的街道也是同一条。因为还一辆汽车都没有,一架花白瘦马拉的双轮便车在路中间飞奔着。驾驶座上,手举鞭子、脚踏旧军靴,一个50多岁的男人催马用它可怜巴巴的力气绝达不到的速度快跑;旁边坐着个12岁上下的孩子,恐惧地抓着他的裤腰。后面,一辆巡逻车正在追他们,副驾上的警察已经两次鸣枪示意,警笛响个不停,不断发出挑衅的吠叫。 那马筋疲力尽、跪倒前蹄,两轮小车轴断了,脱落在后面的车厢飞出去撞上排水沟,把藏在雨布下的东西撒得到处都是,井盖像巨大的硬币沿街滚动再重重倒下。车上俩人迅速爬起来顺着山坡往上跑,巡逻车也一个急刹,两名警察追人,另外两名检查满街的战利品,总共7个井盖。 狂奔。那个50岁的男的瘦、灵活,年轻的时候受过训练,会躲避伏击、在火力逼压下爬过灌木丛、穿铁丝网、举着步枪蹚过急流。孩子呢,12岁的年纪给他的脚插上翅膀。相反,警察身材都变形了,一个肚子跟年龄一样沉重,一个是文员,平常就值值夜班。虽然占优势,但是那男的因为怕枪,跑了大概米的坡之后耸身跳进一堵院墙,儿子也跟了进去;那段墙装了带刺的铁丝网,锋利吓人,不过至少看起来没那么高。 他们掉在另一侧被晨露打湿的草皮软垫上,手、胳膊、腿都被刺挂伤了,然后开始手脚并用地爬,直爬到一条铺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中间的石板路。他们面前有一排结满果子的矮椰树,树后面是一个游泳池,复现着天空的灰色,也是眼前一切的灰色——一切陆续显形并变得真实,像暗房绳上挂的还滴水的照片,在流动的时间里呈现出与事物也许不太有用的相似。 泳池的反方向,湿草坪垫尽头,有一个树阴里的亭子,蜿蜒的石板路有一段拐过去离得很近。一副蕉麻吊床挂在嵌进亭柱的两个圆环上,泥砖地中间一张玻璃面铁桌,周围几把铁艺座椅。 坐轮椅的残疾人就在那儿。一道影子中的影子,同一身睡衣,折到膝盖残株处的裤腿挽个结,用别针别住。他总是起得很早,5点以后就很难再睡了。轮椅后面站着护士,一身板正硬挺的白制服,扣子直扣到脖颈。 光突然一闪,强光,把所有地方都照亮,仿佛日出是一场镁粉爆炸。热气也同时上来了,一种黏人的湿热。独腿人看着那个手脚着地满身是伤的男的,先是定定地、带点嘲弄地打量他,接着微笑起来,脸上露出愉快的惊喜。男人没说话,他身后的孩子先起身、按着肩膀,那儿有血从挂破的衬衫浸出来。他们后面,3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彪形保镖,穿着特别短的薄布衫,用削短型霰弹枪指着他们。 那男的也立起身来,很恐惧,挨近儿子似乎想给他保护,或者从他那儿得到保护。这时候外面有了警察的动静,门铃响个不停。停在人行道前的巡逻车固执地拉着警笛。天蓝制服白围裙的女仆,想处理掉生日会大堆饮料罐、黑色头发闪着水光那个,去后勤门隔着铁栅栏跟警察说过话,又回来毕恭毕敬地站到独腿人面前,还没开口就接到命令去告诉警察:没有搜捕令别想进来,就这样。她传达到最后也是这么说的:就这样。 不仅如此,独腿还做了个强悍的手势命令保镖退下。他们很不爽地回到花园尽头、车库附近——停着辆银色奔驰AMGG,灵车似的黑色雪佛兰萨博曼,还有辆灰色雷克萨斯LS——不放心地从那儿继续监视着这边。 警察的吵嚷渐渐熄灭,听得到他们上巡逻车关门、还拉了两声警笛,最后呼啸而去。这时候独腿转过脸,跟护士低声说了点什么,她消失了一会儿,取回一个小急救箱放在铁桌的玻璃面上。 独腿用一个优雅的手势邀请他们过来处理伤口。孩子先上前。两人都是皮外伤,护士用红药水消了毒,有几处还包了纱布贴上胶带。同时,穿天蓝制服的女仆听主人吩咐,去厨房让给客人准备一顿像样的早饭。她用的原话:一顿像样的早饭。还说了客人。 现在A、B两个开篇合龙,故事要沿着同一河床流动了。跟儿子一块儿捡空罐子或者偷井盖、某天清早被警察追捕的男人,知道,或者曾经知道怎么躲避伏击、在火力逼压下爬过灌木丛、穿铁丝网、举着步枪蹚过急流,对于这个故事来说,是同一个人。 独腿在两种设想里也都是同一个人。得了糖尿病,一条腿截肢,脸色很差,肌肉萎缩,但他年轻的时候,跟刚刚被处理伤口的男人一样,也知道怎么躲避伏击、在火力逼压下爬过灌木丛、穿铁丝网、举着步枪蹚过急流。 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3年,截肢是因为小腿坏死;但是他出了名的生日会还年年操办,每次请来二百多人快活到天亮,哪怕他现在只能喝健怡可乐,大家也纷纷到亭子里停着的轮椅跟前露脸,在两个轮流登台的乐队陪伴下——上次从蒙特雷请来“暴响炸药”,还有洛杉矶的“北虎”——人人逍遥自在。 最后一次,排场最大的一次,是几个星期之前为他的50岁生日举行的;派对证明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老,是这病拖了后腿。就连从来不参加聚会的革命总司令,也出于充分信任前来捧场半小时。 独腿,一位职业律师,没有任何公职也不是党派人士,但从幕后操纵着整个国家的司法机器,包括宣判裁决的法官的意志,不管是刑事、民事、劳动纠纷,没有他点头都不会发布到财产登记公告里。这是一项赋予他的权力,他用得很谨慎,也游刃有余,从来不会弄错接到的指示,也不容许他的传达发生执行上的偏差;他自视为这架碾碎敌人、维护自己人的机器上最重要的传动杆,给委托者和他本人(以相应比例)肥厚的回报——他喜欢“肥厚”这个词儿,不常见,听着有点犬儒的味道。 他很年轻就离婚了,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某年圣周六从温泉回来,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死了,得了红斑狼疮的医院,两人都单身,所以他不会有后代了。遵照他再荒谬也没人敢质疑的指令,两个孩子的房间永远整洁,床单每周都换,洗手间里毛巾架上挂着散发清洁剂味道的毛巾,皂盒里有整块的香皂,衣帽间的衣架上挂着他们的衣服,空调运行的蜂鸣声永不停止。 穿天蓝制服戴围裙的女孩拿桌布铺上铁桌的玻璃面,把红药水、胶带、剪刀和伤药收回急救箱,然后摆上餐具。独腿让催厨娘赶快备好早饭,像个迫切地要上台的演员等着幕布拉开,不想让任何服务员、酒杯和咖啡壶走来走去打断他的故事,天蓝制服女仆,笔挺的护士和紧身薄衫的保镖竖起耳朵,心无旁骛地等着他开口。 他要讲的事和那个满身血污、被铁丝网的尖刺挂得破衣烂衫的男人有关。哪怕天不亮,他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过去很多年了,但他的样子还记着。忍受疾病折磨、困在轮椅里、在这世上孑然一身、尽管素有犬儒的名声而且“犬儒”已经成了冷血的代名词,他还是自以为是个心胸豪迈的人。我是个心胸豪迈的人,他对着按指示从后面靠前、附耳贴来的护士说,尤其当过去的事浮现眼前的时候,你看那边那个男的,那个带着孩子偷井盖的贼,就像我兄弟一样。曾经像我兄弟一样,他改口说。 早饭终于上来了,独腿人开始情绪激动又开玩笑似地说起他憋了好久的故事,而且认为对方也感同身受,每讲到一个地方都要寻求共鸣,让人家证实自己的话。 而那个男的只管吃,每吞下去一口都瞪大眼,好像完全不信这是真的,孩子下手抓着,两边腮帮子鼓鼓囊囊。像这样的一顿早饭,橘子汁、切成大块的水果、西红柿裹蛋、加肉丝的菜豆炒饭、大块的油煎奶酪、刚出锅的玉米饼、烤面包、甜面包、黄油、番石榴酱、加奶咖啡,可不是他们平常能吃的;他们的一天从清早站着吃饭开始,摸着黑,推车上街拾荒前,在辛克区那间放着摇摇欲坠的桌子的小屋里,这间屋既当厨房又当卧室,全部吃食也不过是一点掺水的咖啡,一小块冷面包爷儿俩分着吃,每天晚上男人都把面包拿报纸裹上,怕蟑螂咬。男人的老婆,孩子他妈,到哥斯达黎加碰运气去了,再也没她消息。 我们已经知道独腿不能吃任何他用来待客的食物,他时不时地停下讲述,咬一小口烤得半焦的面包,护士负责往上面涂一种名叫“我不信这不是黄油!”的代黄油,再蘸点代覆盆子酱,果糖做的。喝的是寡淡的母菊茶。 不过是时候听听独腿讲的什么了。他所讲的事关于号山丘,也就是年反索摩查独裁的解放战争中,米拉福洛雷斯山在军事地图上的代号。那座山靠近哥斯达黎加边境,位于尼加拉瓜湖和太平洋中间地带,离埃尔奥斯蒂奥纳尔沿海村镇很近,整个区域为高度不大的山地,每一座都编上号,被双方殊死争夺,经历了多轮的进退攻守。这使它成为南方阵线“本杰明·塞勒通”所代表的游击力量和国家卫队之间真正的阵地战,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争夺一直持续到其他游击阵线向马那瓜汇合、索摩查被迫逃离该国。 当时那个男的和独腿都属于“伊万·蒙特内格罗”纵队。他们在哥斯达黎加会合,在阿莱纳尔火山附近一座庄园接受军事集训,后来被派往利比里亚,出发时住在同一处安全住所,两人都已接受武装编队,准备穿越国境线;不仅如此,这个在狂吞海塞的男人曾是他的长官,你们看到的这位曾经是我的长官,我们分队的队长。你们能想象吗,我得听他的,按他的口令稍息立正?甚至撒尿都得向这家伙打报告,顺便说下,他脾气很差的。独腿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他们在同一战壕作战,分吃煮香蕉和菜豆大锅饭,甚至同享过负责送饭的16岁女孩,那是埃尔奥斯蒂奥纳尔一个渔民的女儿,但这事儿你可不知道,兄弟,谁知道你会怎么罚我。好像要为他所坦白的浪荡行为辩白,他转向护士,战争就是这样,他说,就是个屌球,还耸了耸肩膀。 他从格拉纳达的家里逃出来,逃离家族和姓氏,中断了马那瓜耶稣会大学的法学专业,多年之后才复学,只为加入游击队。南方阵线人声鼎沸,他们本可能根本无缘谋面,但命运将两人安排在一处,从他们在阿莱纳尔火山军营遇到直到战争结束后坐着同一辆运牲口的卡车胜利进驻马那瓜,在那里咱们失去联系,到现在,兄弟,多少年了?独腿问那个男的,你算算,三十年,怎么说的来着,倏尔一瞬。 终于填饱肚子的中年男人,和先前一样定定地看着独腿。他失神地打了个嗝。这家主人的权势人人皆知,要见他一面得在前厅等上好几天,但这声望却没法传到一个靠偷井盖和在垃圾堆里捡空罐子过活的人耳朵里,这人连身边的新闻都不知道,因为他的半导体收音机好几年前就不能使了。 他完全不知道残疾人在桩桩司法案件中得的好处,这些案件的处理全看他偏向哪边,他从毫无防备的投资人手里剥夺的海滨房产,多少公里的海滩,一个接一个的海湾,其中有些离埃尔奥斯蒂奥纳尔很近,号山丘隆起的地方;所有他收的地将来会建成五星级酒店,退休外国人的生活社区,捕鱼和休闲游艇的船坞,高尔夫球场。如果有人不想卖地,他的地权将会失效,或者出现武装农民群体,以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条款为由据为己有,逼得不屈的土地主人束手就擒,把地转让给某个有限公司,而这种公司残疾人的公文包里有好几打呢,都是最好的地。 也不能怪独腿不对那男的说这些。这种事就算是他珍爱的孩子们还活着,他也不会对他们讲。他讲的还是同样的故事,浸满雨水的战壕,阿根廷独裁政府送给索摩查的喀秋莎大炮从远处射来的榴弹激起泥土和碎石的沙幕,从马达持续不断的轰响和机翼遮挡阳光的阴影来判断是否已经靠近的双反轴螺旋桨飞机,它们随后会投下炸弹,把野间寥寥无几的大树熊熊点燃,还有那绝大部分在水上炸开的投射弹,就在海滩附近,那是索摩查海军玛梅尼克阵线的战船投过来的,船上仓促装备了无后坐力炮。他又说起两人都发生过关系的16岁女孩,现在独腿想起来她叫苏珊娜,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不是处女了,不知道跟你什么情况,是不是你破的,他对中年男人说,为给这个段子添彩,还爆出一阵猥亵的大笑;身后冷漠的护士、忙着收拾残羹的天蓝制服女仆、男人、孩子都没什么反应,倒是在车库旁边听着的保镖们有所反馈,恭顺地,在笑的时候露出大牙。 其实中年男人只想走人,可他惧怕大门和门外的情况,警察可能就在外面等着。他的老马怎么样了?筋疲力尽躺在大路上,连同散架的小推车,可是他最值钱的东西了。他不做声,不是因为不知好歹。这个残疾人不仅没告发他,还撤去了荷枪实弹的保镖,给他和儿子治伤,又给他们吃了顿饱饭。他沉默,因为那张因疾病而衰老的脸让他茫然,可能这人确实在他的小分队里,但他不记得了,他手下有12到15个人,那以后都没见过,他记不起他们的脸,就像不记得战场上死人的脸一样。 有时饭菜倒的确从埃尔奥斯蒂奥纳尔送来,这要看情况,有没有轰炸,国家卫队有没有反攻,但在他印象里,送饭的活儿苏珊娜从来没做过,都是男同志负责的。可能独腿就喜欢用这个名字叫人吧。他自己是在海滩上认识的苏珊娜,一次下海洗澡的时候。下海需要纵队批准,三四个人一组在天亮前偷偷地出营,一个人放哨,其他人让大浪冲掉一身的泥污,然后重新穿上搁在沙滩上的汗津津的制服,被泥浆浆硬的靴子和战斗装备。 当时苏珊娜穿仔裤和一件尼龙衫,她转过身子,胸罩就从衫子里透出来。是红色的。她冲他笑笑,用双手往脸上撩水。他们没怎么说话。他建议,跟闹着玩儿似的说,当天晚上在镇子和营地中间的一个地方见面,没想到她答应了。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她在哪儿见的独腿,如果俩人真见过? 进驻马那瓜后一个星期,苏珊娜来找他,几经打听,在索摩查的别苑找到了他。那里已经是南方阵线的驻地。他们一块儿过了几年,他给当时的一个指挥官当随从。后来就厌烦了。他想不起来自己是申请了退役还是逃走了。那会儿当逃兵不是什么大事,没记录、没档案、也没真名,只有化名。他叫亚伯。独腿叫什么? 后来他什么都干过,城市巴士售票员、电力材料仓库看守,他从那儿拿走了一卷电线,头一遭进了蒂皮塔帕模范监狱。那里满是国民卫队的守卫,正是他在南方阵线的对头。后来又在东方市场搬过筐,在红绿灯路口卖过小商品。苏珊娜卖过彩票,然后干上了扒手行当,带着一把鞋铺的小刀,游荡在商贸中心假装看橱窗,却用刀划开女人们的钱包下手,直到有一天桑地诺阵线的警察抓住了她。放出来后她就一个人回埃尔奥斯蒂奥纳尔去了,两人再没见过。往后他又认识了第二个女人,给她生了这个儿子,抛下小家伙到哥斯达黎加找出路了。独腿在打仗那会儿是不是也和苏珊娜做过,或者是不是把她和另外一人搞混了,因为她从没到营地送过饭,这一点他很清楚,现在他都不想明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就算真是这样,他也不会因为这事儿就不感激对方。苏珊娜的样子他也不太记得了,哪怕现在在大街上遇到,谁知道还能不能认出来,搞不好连牙都没了。 他又惦记起他的马,却见独腿让护士推着轮椅靠过来要拥抱他,也拥抱了他。现在他说着,再次提高音量好让所有人都听见,说他永远感激亚伯同志救了他的性命。他们一直叫你亚伯吗?站在这里的这个人救了我的命,我们正在跑步撤退,国家卫队正在冲击山头,我们放弃了战壕,勃朗宁MA4重机枪的枪手已经死了,阻挡不了敌人的推进,突然我膝盖好像被蚊子叮了一下,原来是被手榴弹弹片击中,我跪倒在地,孤立无援,敌人近得都能看见从灌木丛里的头盔了。是这个男人回来了,冒着枪林弹雨,匍匐爬到我身边,用尽全身的劲儿把我拉到其他人隐蔽的那块洼地。要不是他,我已经没命了。 独腿讲的这事男人倒想起一些。但他那样做不止一次,顶着敌人火力折返,去救他手下的落在后面的战友,有人中枪,有人是被弹片击中。有一回纵队队长还说要授给他一枚勋章,但是那会儿没有什么勋章,到有了的时候,已经不是打胜仗的日子了。没人还记得他被称为“远超出职责范围的英雄主义行为”,或者真要给他授勋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已经退役或者逃走了。谁是队长来着?不记得他的名字了。高个儿、壮汉、金发、大胡子、很固执的一个人,但是名字记不得了。那人早中晚餐都吃一罐沙丁鱼,只吃那个,永远散发着沙丁鱼的味道,呼吸,汗水。 独腿又拥抱了他。真快要秃顶了。鼻子里是尿和古龙水混合的味道。他不知道对方有小便失禁的问题。头顶稀疏的毛发,尿臭味,截断的腿,使他产生一种既怜悯又厌恶的情绪。他绝不想看到自己坐在轮椅上,往挂在椅背上的塑料袋里撒尿的样子。 终于,到了走的时候。快八点了,家里活泛起来。司机进来,园丁出现,更多的保镖,助理律师,两个秘书,独腿在他家的另一翼有好几间办公室。一个秘书奉命去取了钱,五张百元科多巴[1]大钞,崭崭新。他递给他,带着最后一丝作为同谋的愉快微笑。独腿还在激动地重复,看着所有人的脸说:“他救了我,就是他,这个男人救了我的命。” 你可别没影儿了啊,分手的时候他说,用得着的时候,你知道我会帮你。别再偷东西了,干这个早晚代价惨重,这个孩子我们送去上学。你可以跟着我,做园丁,或者到我哪个庄园去。男人注意到他说的不是我的庄园,而是我的哪个庄园。你可以在咖啡园干活,或者奶牛场,随便。当拖拉机手也行啊,学学开拖拉机。 男人收下钞票,赶紧放进兜里,好像拿了什么不干净的钱。害怕上街的恐惧已经消失了,因为一个司机奉命要把他和儿子送到要到的地方。上了装有偏光玻璃的黑色雪佛兰萨博曼的后座,有皮革和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司机用不放心的眼神从后视镜看着他们,问去哪。辛克区,把我们放在红色蓄水池那儿就行。男人小声小气地回答。 司机开车路过他那散架的小推车,还在路上搁着,没人拾掇。也没人管那匹死马,周围全是苍蝇。 马那瓜, SergioRamírez,Floresoscuras,Madrid:Alfaguara,SantillanaEdicionesGenerales,S.L.,. [1]科多巴,尼加拉瓜货币单位。 本文节选自塞尔西奥·拉米雷斯·梅尔卡多作品《号山丘》。译者:于施洋、蔡潇洁。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李瑞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ly/3520.html
- 上一篇文章: 沪大胖说球尼拉甲马那瓜捍卫榜首宝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