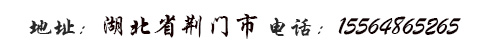我的菩提路519張志成正覺的
|
01.前言 :正覺同修會(蕭平實私人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五輯《我的菩提路》裏面,你讀到所有「見道報告」似乎都煞有介事地告訴你「我們找到了自佛陀出世以來千聖不傳第八識真心」!上兩篇文章我們説明「找到第八識」不是「現觀」(無漏智慧),第八識也不屬於意識的「現量」認識範圍,「第八識」是意識根據蕭平實理論產生的幻想。 張志成老師在上一篇文章中誠實地告訴大家,正覺同修會刻意挑選出來打廣告的「見道報告」裏面,雖然沒有刻意的造假的成分,但是其中的「現觀第八識」、「觸證密意」、「心得決定」都是被洗腦、暗示、引導之後「腦補」出來的内容。張志成老師被印證時的「疑惑」很多人都曾經提出,只是絕大多數人都以爲上禪三探究「開悟密意」就可以「釋疑」,而禪三知道答案後生起的不解和疑惑,一般都會被莊嚴肅穆的「選佛場」氛圍和蕭導師的宗教權威抑制壓止。 爲什麽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信而不疑?除了人性弱點、宗教神話,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從來都不知道佛法的「觀行」是什麽! :寫這幾篇文章時,琅琊閣師兄問我:張老師你學法讀經這麽多年,經歷了密宗、現代禪、本願念佛和正覺同修會,怎麽可能連觀行都不會?觀行難道不是學法最基礎、最核心、最重要的功夫? 坦白説,我在去年之前真的不知道真正的觀行是什麽,我讀佛學書籍和經論這麽多年,對觀行的理解非常膚淺。直到去年聼經圓師兄講解正知而住、五蘊觀、六入觀、唯心識觀,才知道佛法的實修和觀行,是要自己直接操作的,如果不實操,就算每日讀萬卷書依舊是紙上談兵。 這一篇文章篇幅雖然比較長,其實沒有太多經論教理,只是引用了許多正覺書籍和《我的菩提路》裏面的「觀行」文字,希望讀者瞭解正覺的觀行錯在何處。這些錯誤用三個字總結就是「不如實」。 至於正確的觀行方法,請參考文末的鏈接。 02.正覺的「佛法十八界+醫學科學」觀行法? :「觀行」是佛法實修的核心,是修行證果的必備功夫,但是在正覺同修會,不但上課不教觀行,學員之間討論觀行都被全面禁止。除了《我的菩提路》那些到處圈圈方格的「密意觀行」,正覺的書籍視頻講課不講解應該如何觀察五蘊十八界,禪三上你能猜到密意,被印證,自然就會知道走路、喝茶的「觀行秘密」。 下面框框裏面的,是化名方竹平的正覺親教師張正圜,在《佛法真實義》(又名《佛法概論》)68-69頁中,針對五蘊十八界所説的「觀行」範例,是正覺書籍裏面很少出現的内容:(宗教文化社年版) 物質世間衆生舉凡身口意業之造作,均不離十八界之範圍。如以吃蘋果爲例:吃之前由眼根接觸蘋果的形狀、色彩、明暗、大小等色塵,眼識辨別蘋果的形狀,色彩暗紅,大小適中等狀況,此是眼根、色塵、眼識三界之運作。 眼識辨別蘋果之色塵,同時轉變為訊息,知會意根。意根接受眼識傳回來在色塵訊息,由意識依據過去之經驗而分別這是蘋果,顔色暗紅,大小適中、形狀正常,看起來很好吃。這是意根、法塵、意識三界之運作。 經意識辨別後,末那識決定要吃蘋果,身根便拾起蘋果,經由手的觸覺知道蘋果的軟硬、粗細、光滑(觸塵),即於送入口中之同時,將觸塵轉變為訊息,經由意根告知意識,這是身根、觸塵、身識三界之運作。 蘋果即將送入口中時,由於香塵之飄散,鼻根經由呼吸而接觸香塵,鼻識辨別蘋果香甜之香塵,同時將此香塵轉變為訊息,傳與意根,意識綜合眼識、身識、鼻識對此蘋果所傳來之訊息,繼續作判斷,如果蘋果已經爛壞,則棄而不吃。這是鼻識、香塵、鼻根之運作。 蘋果送入口中後,身根經由口之咀嚼,產生震動聲音,耳識經由耳根接觸身根震動之聲音,同時接觸口齒從空氣中傳來之咀嚼聲,而辨別聲塵之大小聲、長短聲、粗細聲、高低聲,同時將此聲塵轉化為訊息傳與意根,此是耳根、聲塵、耳識三界之運作。 口齒咀嚼蘋果,分泌口水混合,舌根接觸蘋果,舌識經由舌根辨別蘋果之甜味(味塵),同時將味塵轉化為訊息,傳與意根,此是舌根、味塵、舌識三界之運作。 以上説明眼識經由眼根知悉蘋果之色塵,耳識經由耳根獲得蘋果之聲塵,乃至意識由意根獲取眼、耳、鼻、舌、身等五識對五塵之基本訊息,而由意識依據過去之經驗判斷此蘋果之各種情況,而分別、思維、判斷應否繼續吃,再由末那作決定,導致身根再取食,或棄而不食。如此便完成了六根、六塵、六識等十八界之運作。 實際上,十八界之運作情形,遠較前面的説明複雜十百倍,速度之迅速完美令人難以想象。爲了方便説明,依六根分爲六個部分分別解説,但其實六根總是同時連續不斷在配合運作。衆生在日常生活中之各種活動,都離不開十八界之運作,而竟對於十八界之運作細節及各界差別與和合一無所知,一無所感,懵懂度日,以致六道,受苦無盡。由前五蘊、十二處之詳細説明,即知六根、六塵、六識等十八界,非本來自在之法。因此在這十八界當中并沒有真實的我,都是變異無常之法,所以無常、無我、空。若能如是斷除對十八界我的執著,便可出三界輪回,免去生死輪回之苦。 上面張正圜敘述的十八界觀行,雖然沒有禪三喝水的「觀行」細緻,理路完全相同。這種「觀行」爲什麽不是佛法修證的「觀行」? 錯誤1:「佛法十八界+醫學科學」的「如來藏生理學」觀行法 我們在群組討論上面這幾段文字容時,南伽他師兄將之形容為「佛法十八界+醫學科學」的怪胎觀行法——比如「鼻識辨別蘋果香甜之香塵,同時將此香塵轉變為」,是什麼法?是什麼界?是色?是識?是心?鼻識將香塵轉變為?鼻識有這種神奇的轉換能力?能夠轉換色法?佛法觀行爲什麽出現現代醫學和科學採用名詞和概念? 錯誤2.:無法斷我見 二乘修行要觀察現象的共同特質是無常、無我、空,這個説法本身沒有錯,但是上面描述的觀行有沒有直接觀察「苦、空、無常、無我」的内容?從二乘斷我見的角度來説,上面的「十八界+醫學科學」沒有直接觀察「現象無常、無我、空、不自在」,也不涉及四聖諦和因緣法的觀察,更加沒有指出在吃蘋果的整個過程中,凡夫在哪一蘊、哪一界增益了「我見」,產生了一合相的錯覺。阿含經裏面證果的人,是用「十八界+醫學科學」的觀行方式斷我見嗎? 錯誤3:無法破法執 從大乘斷法執的角度來説,上面的「十八界+醫學科學」沒有觀察蘊處界現象的本質都是變動的、不穩定、不恆常、不獨立存在的——般若經所説的的「無自性、無所得」。《心經》説「五蘊皆空」是「無眼耳鼻舌身、無色聲香味觸」,上面的敘述,「有眼耳鼻舌身、有色聲香味觸」,一切法真實存在,一個不缺、一個不少,還多了沒有被歸類於「蘊、處、界」的訊息、呼吸等法,還要你在「有眼耳鼻舌身、有色聲香味觸」再加上一個常住第八識。 佛法修行是要破我執、法執,正覺的觀行是要「找第八識」。大乘經論和禪宗文獻裏面,有正覺的「十八界+醫學科學」觀行方式?哪位祖師知道「眼識可以將色塵轉變為訊息」這種現代醫學知識?歷代祖師是用這種觀行方式開悟的? 錯誤4:不如實——用想像替代「觀行」 上面這段文字雖然有個別句子是吃蘋果的現前體驗,但是大部分都是對感知過程的理論敘述。 「身根便拾起蘋果,經由手的觸覺知道蘋果的軟硬、粗細、光滑(觸塵)」這句話是形容吃蘋果過程中的直接體驗,但是「眼識辨別蘋果之色塵,同時轉變為訊息,知會意根。意根接受眼識傳回來在色塵訊息,……經意識辨別後,末那識決定要吃蘋果……」這句話是直接的體驗嗎? 你可以直接體驗獨立於其他識的眼識嗎?可以體驗眼識將色塵轉變為訊息,知會意根?這些你無法直接體驗,純粹根據生理學教科書内容陳述描繪的「知識」性内容,可以讓你找到凡夫在五蘊上增益的我見嗎? 今天看正覺的觀行,覺得錯得很離譜,但是多年以前,當我最初接觸「正覺佛法」的時候,覺得上面這些説法理所當然。爲什麽當初不懷疑「眼識辨別蘋果之色塵,同時轉變為訊息,知會意根」不是現前體驗,是推理想象?這一切或許要從識的分類説起。 03.我們如何將「識」分類切割?如何體驗識的存在和功能界限? :上一篇説過前六識的存在是世間法和三乘所共許的「世間現量」。世間現量是説,我們可以直接感知前六識認識的對象,以此體驗前六識的功能;但是,不等於說我們能夠「看見」前六識、能夠「直接觀察」它們的運作。 如果可以「直接觀察」它們的運作,我們應該可以感知大腦裏面有一個屬於末那識的區域,這個區域獨立於其他的識,然後你做決定的時候,是這個部分在運作。或者,一個盲人應該可以直接感知自己大腦裏面與視覺有關的部分沒有功能,一片死寂。這種才可以稱爲直接的感知和體驗。 再以眼識為例,所謂「眼識在觀察什麽」,是我們根據已知的眼識功能推論它有生起、有功能。我們無法直接用眼睛看到眼識,也無法直接體驗眼識獨立於其他識的存在,只能根據經論對眼識的界定,推論「辨別顔色」這個功能屬於眼識。至於區分眼識與意識,眼識與意識同時生起,你如何切割兩者,直接憑感覺區分出獨立於眼識的意識,或是獨立於意識的眼識? 換句話說,我們對前六識的認識,必須通過經驗性的感知、類比推論識的功能,才能區分出不同的識。 :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經論所説的識的「三種分別」——自性分別、隨念分別、計度分別,這三種分別是可以直接體驗的嗎? :八識的三量和三種分別,都是基於聖言量和理論的分析,根據具備很强的定力和觀力的修行人的體驗,將感知過程中的不同性質和階段拆解。 比如,當你去看一個白色的杯子,一個定力和觀力都很强的人可以現前觀察、體驗的是以下的眼識、意識的功能: 一、不起概念的覺知「所謂白色的杯狀的東西」, 二、覺知對此東西生起的「沒有語言文字的概念」──獨立的「白色瓷杯」的感覺, 三、覺知對此東西生起的「語言文字概念」, 四、覺知對此東西生起的各種覺受、貪瞋等的煩惱。 :沒有定力和觀力的凡夫,活在「自言自語的概念世界」而不自知,最多只能觀察到上面的第三、第四階段,無法察覺到前二階段,對自己的執著、煩惱只有非常模糊的、後知後覺的察覺力。 :如果我們用「三量」和「三種分別」的定義,可以這樣分析「看到一個白色的瓷杯,然後生起想法、貪念」這個過程: 第一剎那:看到一個白色的東西,是率爾心的眼識以及眼俱意識 這時的了別是一種不起名言概念的單純覺知——「現量」的「自性分別」,這種分別也稱為「無分別」,所有五識以及第八識的了別根身、器界皆是屬於此類的「現量自性分別、無分別」。 第二剎那以後:凡夫的意識一般都是接續生起「隨念分別」,抓取過去的經驗記憶比對,生起這是「白色的」、「材質是瓷的」、「喝茶用的茶杯」等概念,此時的意識所作的不是「現量的自性分別」,而是「比量」的正確判斷或是「非量」的錯誤判斷。 接著,可能生起各種推測、想像的「計度分別」,這些推測想像可以是「比量」,也可能是「非量」。 第七識的「計度分別」是針對第八識見分所生起的我執、法執,不是意識可以察覺,是「不可知」的;「可知」可察覺的「計度分別」都是意識的內容。以此例來說,意識會計度「白瓷杯」是「好看的」、「值錢的」。 再接下來,就是因為「計度分別」所引發的各種執著、煩惱、行為,可以歸為意識的各種心所。譬如「我很喜歡這瓷杯,即使沒錢也非擁有不可」這種貪心所。 只有當你具備强大覺照心念的能力,然後再配合經論裏面五蘊、六入、十八界、或是百法等法相的定義做觀行,才可以觀察到: 一、不起概念的覺知「所謂白色的杯狀的東西」:「眼識、率爾初心眼俱意識對顯色、形色的自性分別」,其實此時「眼識」與「眼俱意識」是區分不開的,只是一個「對顯色、形色的自性分別」。但心不夠細或不誠實的人,可能會以佛學知識或思惟結果來「對號入座」,而其實完全沒有現量觀察的實質。 二、對「所謂白色的杯狀的東西」生起的「沒有語言文字的概念」──「白色瓷杯」的感覺:「眼俱意識」對顯色、形色的隨念分別,實質是意識想心所中不起名言的取相功能。若能察覺此,就能分別「意識」與「眼識」的不同。 三、覺知對「所謂白色的杯狀的東西」生起的「語言文字概念」──這是「一個白色的瓷杯」:「獨頭意識」的想心所、表義名言的功能。若能察覺此,就能經驗性的區分意識想心所中的「不起名言的取相」與「表義名言」的不同。 四、覺知對「所謂白色的杯狀的東西」生起的各種覺受、貪瞋等的煩惱:意識的受、想、思心所以及別境、煩惱等心所法。 即使定力很强、觀察夠細,也無法直接看見眼識、或是體驗眼識獨立於其他識的單獨運作,只能經由上面的感知過程,藉助意識的類比推論功能,再根據經論的定義,區別出眼識與意識的功能界限。 修習「正知而住」、「看話頭」這類功夫的最主要目的,是先減少念想與煩惱,然後,才有能力「現量」或「比量」的去察覺「語言文字概念」生起之前的心識狀態,但是,要感知到意識第一念對杯子的「現量認識」與後面意識帶有概念、推論、分析、命名的「比量認識」,需要非常強的定力才有可能,即使是修行人也無法輕易做到。 這些感知不到的内容,不是我們可以「觀行」的對象,也不是斷我見所必須觀察的内容。上面的這些觀行,不管多麽深細,依然不脫離世俗諦、安立諦的範疇,與二乘、大乘見道的無漏智沒有關係。 :「識」在經論裏面是按照感知對象和功能來區分,心識對顔色、聲音、觸覺、味道、甜酸苦辣的感知、分析、推理、記憶等功能……我們確實可以直接體驗。但是,不等於我們可以直接體驗整個感知過程、不等於我們能夠直接體驗識在何處生起,不等於我們可以直接區分一個識與另外一個識的界限。 識的分類本身就是人爲的切割劃分。 如果你問一個小孩子或沒學過佛法的普通人:你有幾個識?他會説有六個嗎?如果你問一個科學家、心理學家、腦神經專家同樣問題,他們的答案也未必一樣。答案不一樣,因爲識的分類是人爲的切割,「識」不是像清楚五個手指頭那樣可以明確地數清楚,分開在大腦裏面直接分開六個或八個。 人有六識或八識這個認知,是後天學習的分類法。如果按大腦功能分類的話,可以分出很多個功能區:控制身體各部分肌肉,管理情緒、邏輯、想像力、視覺空間、語言等等。即使在佛法裏面,阿含有六識的分類,唯識有八識的分類,《攝大乘論》也有十一識的分類:(一)身識,(二)身者識,(三)受者識,(四)彼所受識,(五)彼能受識,(六)世識,(七)數識,(八)處識,(九)言說識,(十)自他差別識,(十一)善趣惡趣死生識。 識的功能界限不是直接體驗,而是反推所得,這一事實在正覺的見道報告裏面有很多例子,比如見性親教師王美伶在《我的菩提路(二)》頁寫道: 「也就是說,你怎麼確定你找到的就是祂?我一時也傻住了,只能回答「觸證」的那一刹那,就確認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清楚七轉識各自的功能之後,□□□□□□了!」 蕭平實將「觸證第八識如來藏」等同於真見道,這個説法違背經論之處已經從不同角度辨析過。 阿賴耶識是初地以上菩薩才能「證解」的法,經論裏面「觸證」一詞可以與智慧、禪定、樂受連接,經論關於大乘見道的文字,有很多「觸證真如」的文字,但是沒有「觸證如來藏」、「觸證阿賴耶識」的文字。 「觸證」是直接的親證,真見道「觸證真如」是一個現量認識。如果你能夠直接「觸證第八識」,「現量認識第八識」還需要用排除法——排除七轉識的功能——證明自己找到的就是第八識?你應該可以直接形容第八識的功能,其分別的對象是什麽才對!如果我直接看見一個蘋果,直接感知第八識如何認識如何持身,我需要用排除法說這個是蘋果,因爲我知道它不是梨子和桃子嗎?我需要排除其他識的功能,才能證明觸證的是第八識? 排除法是思惟推理,不是「觸證」。 王老師與正覺所有的「明心菩薩」,是怎麽用排除法「找第八識」?「我清楚七轉識各自的功能之後……」——當你熟讀蕭平實著作、概念界定清晰,無需拜佛,就能夠清楚蕭平實所界定的「七轉識各自的功能」,確定剩下的那個「功能」就是蕭平實界定的第八識的持身功能。這個功能不是阿賴耶識持身的結果,只是百法裏面三位差別的「心不相應行法」,如果用五蘊歸類,屬於行蘊。 再者,王老師說「我清楚」而不是「我現量、現前體驗」七轉識的功能。意根末那識與阿賴耶識一樣,只能通過「聖教與正理」才能證明其存在,不是前六識可以感知的對象。你如何直接體驗是第七識在做決定而不是意識在做決定?難道做決定那一刻,你感覺到大腦裏面有一個單獨屬於意根的區域有反應,另一個屬於意識的區域沒有反應?如果真的是「現前直接的觀行」,不是意識按照定義反推和對號標記,一個普通人如何將一個一體的感知功能,劃分為眼識、身識、意識、和意根末那識? 張老師,爲什麽要將人類的感知功能、對象和過程做標簽、分類、拆解?這與解脫、破執有什麽關係? :佛法「觀行」的目的要看清諸法(現象)的特質和屬性——稱爲「自相」和「共相」,二乘人看清的實相是「人無我(我空)」、「四聖諦」,大乘修行人看清的實相是「人無我(我空)、法無我(法空)」,又稱爲空性、真如。 一個世間人對現象的認知是非常粗糙,後知後覺的,活在「一合相」的妄覺裏面,連自己對某人某物生起了什麽覺受概念都不察覺,當然更看不到其中的「一合相」。佛法的修證,目的是生起我空智、法空智而破除我執、法執。 要破執,比如破除有一個「常、恆、不變我」的執,首先要將「一合相」分拆——可以拆解為色心二法、五蘊,或是六入,十八界,甚至是百法。拆解的重點不在於分類多細緻,也不是要藉助醫學名詞巨細靡遺地描述感知的過程。 重點一,能否通過拆分「一合相」,找到實我見、實法見的所在,能否看到「苦、空、無常、無我」、「空性、真如」的實相? 重點二,觀行是不是當下的、直接的觀察體驗?推理和想像沒有破執、生起無漏智慧的效果。 重點三,用「五蘊、六入、十八界」的分類去標記現象,目標是斷我見,最後證大乘的「五蘊皆空」,也就是説,標記的目的是消除錯覺(我執、法執),斷我見時「唯有諸蘊可得」,最後證得大乘見道「二空所顯真如」時,沒有任何標記。 試想,一位醫師對吃蘋果整個過程的感知和分析,一定比張正圜或是正覺任何一位老師都細緻深入,按照正覺的説法,所有的醫師,應該比普通人更深入直接地體驗「苦、空、無常、無我」,他們讀完醫學院應該全部都能輕易斷我見才對? 04.正覺的「觀行」是標記、配對、推理、幻想? :觀行必須是正對著一個對象觀察。 當我們做觀行,做「現前觀察」的時候,我們是對著一個可見或是不可見的對象(比如杯子或是自己的覺受),觀察它的内涵、它的變動、它的本質。不管是粗糙的體驗觀察,還是用定力和觀力去觀察分析,都是正對著一個對象觀察。 正覺所謂的「現前觀察前六識」,是根據經論的分類和定義,思惟推論,對號標記。 比如張正圜説的:「末那識決定要吃蘋果,身根便拾起蘋果,……」; 比如正覺的見道報告裏面,經常出現的走路體驗真心妄心合和運作的「觀行」:「我睜眼經行時,眼識做了什麽、意識做了什麽、意根做決定、然後我的脚往左邊邁了一步……」; 在上面的兩個例子裏面,「身根便拾起蘋果」、「脚往左邊埋了一步」是直接的體驗。 至於眼識觀察到什麽、意識做了什麽,末那識決定了什麽,都是對號標記,不是可以被現前直接的觀察,因爲你無法區分獨立的眼識、意識與末那識,所以這類形容不管是否正確,不管多麽精確細緻,都沒有破一合相、生起無漏智慧、破執解脫的效果。乃至「末那識決定什麽」是一個連理論都完全錯誤的標記。 :走路「觀行」體驗真心妄心運作的例子屬於《我的菩提路》裏面比較正常的「觀行」例子,《我的菩提路》裏面有些見道報告出現「耳朵聽到種子流注」等經論中聞所未聞的「體驗」。正覺教團的親教師也經常在課堂上和私下交談中,標榜談論自己如何體驗到「種子流注」,令學員和讀者艷羡不已。 莫説你無法從一個整體的識裏面,經由直接的體驗區分出獨立於其他識的意識,阿賴耶識更是無法被感知、唯有地上菩薩和佛能證解的識。那正覺的「明心菩薩」怎麽看到、聽到、感覺到「阿賴耶識種子流注」? 大部分人造光源都是高速閃爍的,我們看不到因爲人類肉眼只能辨識赫茲以下的閃爍。游正光老師在課堂上多次用平常人看不見的光綫閃爍形容他體驗的「種子流注」。 他所感覺到的「種子流注」其實是修定過程中常見的體驗,到底是什麽很難確定,可能是神經脈衝,可能是其他的生理現象,可能是識的生滅,但是絕對不是「一切種子如瀑流」的阿賴耶識。 最近琅琊閣痞客幫部落格的「大豬師兄」有個非常精闢、讓我捧腹的留言: 阿賴耶識恆轉如瀑流凡夫怎麼觀?正覺同樂會看到尼加拉瓜大瀑布了嗎?經云一彈指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凡夫怎麼觀?正覺同樂會數過了嗎?怎麼能自欺欺人到這個程度啊???? 意識刹那生滅,每一刹那都在思惟、分析、判斷,一秒裏面有多少個刹那?你可以感知到每一秒中意識的變化和運作嗎?而意識只是阿賴耶識含藏的無數種子所生的其中一法,阿賴耶識每一刹那流注無量無數種子,所以才被形容為「瀑流」。 游老師認爲自己感知的是阿賴耶識「如瀑流」一般的「種子流注」,請問如何確定感知到的是「種子」?另外,如果游老師這麽厲害,竟然可以感知到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位修行人、一部經論說可以感知到的「種子如瀑流」,能否數一數在一秒之内意識生滅了幾次,形容意識每一刹那都做了什麽?如果數不清、説不出,說看見「種子流注」是不是太荒誕了! 一個普通人學了五蘊十八界的分類之後,可以用這些名詞概念標記描述感知過程和生理現象,這是正確的描述,但是不是現前直接的體驗。正覺的問題是,讀過唯識的「種子流注」説法之後,隨便將自己的體驗套在上面,變成「我感覺到種子流注」。這種幻想爲什麽可以公開發表在《我的菩提路》裏面?爲什麽有親教師無知到竟然經常公開炫耀?爲什麽「明心菩薩」私下流傳,當作是「我有證量」的證明? :正覺同修會經常不經意的讓學員炫耀這些屬於非量的「境界」,目的是希望藉境界顯示正覺很厲害。其實很多念佛修定的人,都體驗過各式各樣的神異境界,因爲只是境界,沒有人大量寫在書裏,或是講經上課時拿出來炫耀一番,作爲「我們是正法、我們可以現觀第八識」的證明。 正覺同修會因爲分不清現前觀察和推論妄想,慣性將自己的體驗套在無法現觀的教理上,如果認爲自己體驗到「種子流注」就是「現觀阿賴耶識」,等於將凡夫的錯誤「推理」説成是初地見道所得的「現觀」,這不止是亂用佛法名詞,而且是非常嚴重的大妄語。 最近有位劉正莉老師「見性」,搜尋的時候看到網上有發佈她在年寫的見道報告,從她的見道報告可見,從很久之前,這個「將境界套在教理」上的習慣就存在於正覺同修會: 回家時,在台北火車站月台上等捷運,突然聽到捷運車進站的「嗚」聲,很奇妙的,聲音縮小了,跟平常聽到的聲音不一樣;聽法也不一樣,是用「心」聽,不是用「耳朵」聽。這縮小的聲音在心裡就好像「片雲點太清」似的。當時很震撼,生平第一次這樣聽聲音。回到家後,電視的聲音,也是用「心」聽的;樓下小朋友嬉戲的聲音(我家住在第十四樓),也是用「心」聽的。這種感覺,言語很難描述。當時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後來看了導師的書,以及上星期二的課,才知道這些都是意識心的變相;往內反觀的是證自證分;縮小的聲塵是內相分。 上面劉正莉親教師所形容的,是意識在修定過程中出現的情況,攝心功夫深入了,甚至可以進入看不到、聽不到的狀況,但是她直接將「縮小的聲塵」定義為「内相分」。識的「見分」、「相分」、「證自證分」都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對象,只是理論性的説明。何況,聲塵不論大小都是耳識的「相分」,「相分」指識的一部分,如何有内、外之分?如果劉老師不懂唯識,如果這是一位不懂唯識的二乘人的體驗,請問要如何形容「縮小的聲塵」? 再舉一個例子,正覺說「現觀阿賴耶識出生萬法」,你如何現觀阿賴耶識出生萬法?是用意識還是用眼識去觀察?如果是用六識去觀察,那六識必須要比阿賴耶識先出生才可以觀察?不然,六識如何觀察六識自己被阿賴耶識出生? 當正覺拿著六祖慧能的「何其自性能生萬法」作爲阿賴耶識是開悟密意的證明,首先,這句話本來就不是正覺所理解的意思,就算是,如果你不能直接觀察「自性生萬法」,只是坐在那裏推論幻想「阿賴耶識生萬法」,智慧就能生起? :劉正莉親教師的見道報告中,有一道正覺禪三必答題「十八界出生的先後順序」: 至於第二題「十八界出生的先後順序」,是在懺悔前就整理好的:六根先有,再來是六入,最後是六識。意根帶著如來藏進入受精卵,前世意識就永遠斷滅了。此時的「名」只有意根,「色」就是受精卵。如來藏的大種性自性作用,藉著四大元素以及母親體內的營養,胎兒五根漸漸具足;隨著五根漸漸具足,六識才出生。「根、塵、觸處生識」,眼根對色塵產生色入,眼識出生;耳根對聲塵產生聲入,耳識出生;……意根對法塵產生法入,意識出生。此時母親的子宮是胎兒外世界的全部。眼根所見外色塵是外相分,如來藏則相對應現一模一樣的似色相分,稱為內相分。外色塵是物質色法,六識不是色法,故不能直接觸外色塵,只能觸如來藏所變現的內相分色塵。 佛法的觀行必須正對所觀察的對象,經由現前的觀察體驗,加以正確的揀擇,生起無漏智慧。上面這個自己想象推理的「如來藏生理學」答案,到底與破我執、法執,與斷我見,與明心見道有什麽關係? 正覺禪三上的所有問題,不管是持身密意還是「十八界出生的先後順序」,其實都是這種按「蕭平實理論」設計的文字推理題,與禪宗開悟、大乘見道沒有半點瓜葛。所謂「觸證阿賴耶識」也是一個明白蕭平實理論之後,可以用排除法猜到答案的文字題,無需蕭平實神頭鬼臉給「機鋒」引導你,也無需拜佛參究,只不過多了機鋒和參究,求開悟的人以爲真的是經過禪門如喪考妣的一番苦參,得到的必然是貨真價實的「明心見道」。 正覺的「觀行」大致可分三種類型,三種都不脫離思惟想像: 1.認爲「眼識辨別蘋果之色塵,同時轉變為訊息」這個敘述句子是現前直接體驗的人,以爲自己可以直接體驗眼識與意識的界限,分不清理論與現前觀察的界限,以爲佛法是「如來藏生理學」。 2.認爲自己可以現前直接觀察「末那識決定要吃蘋果」、「真心如何持身」的人,誤解經教,分不清現前觀察與推論幻想的界限。 3.一個告訴你他可以「聽見、看見、感覺阿賴耶識種子流注」的人,是將修定出現的體驗套在經論文字上,以爲這就是有修行、有證量的證明。 06.「對比真心妄心」可以「瞬斷我見」? :二乘法的斷我見對凡夫來説非常不容易,但是正覺同修會宣稱,只要你明心找到第八識,然後將這個「真心第八識」與「虛妄的五蘊身心」對比,就會感覺五蘊虛妄,就可以斷我見。甚至你只要聽一聽蕭平實在禪三上面講講十八界的功能,也能證初果,所以學員賣房賣血也要上禪三捧個「初果」回家。 蕭導師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是這樣解釋爲什麽對比真心妄心可以斷我見: 以這個真心來看待色身、來看待妄心、來看待時間、來看待一切空間、一切的事、一切的物,都會跟無常、苦、空、無我相應,因為照見真如、真心、自性彌陀,它的真實、不變異、恆常不變,所以相對照之下,色身變得很虛幻,妄心、妄知、妄覺更虛幻。 一般凡夫眾生、有情眾生都認為真實有一個我,從這個我出發,所以執著於五陰的世間和廣五陰的世間。但是念佛人親證真如之後,我們稱之為親證菩提。親證菩提的時候,他以真如為我,從此不以五陰為我,而真如是一個空性。所以五陰的這個「我」的見解斷除了,「以思惟心當作是我,以能聽能知的心為我」的這個邪見斷除了,以色身為我的邪見斷除了,這叫作斷我見或斷身見。 :在我公開發懺悔文承認自己沒有斷我見之後,蔡正禮親教師私下來信,他的信中也提出導師這種說法: 您誠實承認自己沒有斷我見的功德,末學是隨喜讚歎您的誠實與勇氣。但是您認為自己被印證「明心」而缺乏斷我見的功德,那麼別人也一樣不可能斷我見,也同樣缺乏斷我見的功德,所以「明心」也是假的。這樣以己況彼,並不合理也不符事實。因為末學認為明心「真悟」之人應該要有「瞬斷我見」的功德。因為找到第一能變的第八識當下,對比其不生不滅的體性,必然立即區分出虛妄不實的五陰之範圍,而成就「瞬斷我見」的無間等智。……在鴦掘魔羅的開悟經典中,還特別宣說六見處的法義,作為大乘明心的禪學理論。 蔡正禮親教師與蕭平實一樣,説自己找到一個「不生不滅」的第八識、真心、真我,然後以之來對比虛妄生滅的五蘊,就可以「瞬斷我見」。 前面的文章指出過蕭平實及蔡正禮找到的所謂「不生不滅、常住不變的真心」是佛「從來也沒見過的東西」,是佛陀破斥的「第六見處」,純粹是幻想的產物。蔡正禮不知道「無間等」這個詞就是「現觀」,就是智慧,他與蕭平實一樣都以為「無間等」是「常住法」,自創了一個名詞「無間等智」來形容找到「第六見處」梵我所得到的智慧。 蔡正禮與蕭平實所説,是用佛法名詞組合編造的話術和妄想。爲什麽? 蔡正禮說對比之下「可以立即區分出虛妄不實的五陰之範圍,而成就『瞬斷我見』的無間等智」,正常人比較兩樣東西,這兩樣東西必須都是真實存在,才能掂量、比較兩者的差異。 從經教來説,如果正覺所證是《心經》的「五蘊皆空」,那應該「無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既然沒有五蘊,如何比較?從現前觀察來説,蔡老師所説的「五陰虛妄不實、阿賴耶識是不生不滅」,他所謂的虛妄是指生滅無常。首先,蔡老師何時直接觀察到五陰的生滅?就算直接觀察到,也只是斷了常見。《成唯識論》說阿賴耶識「念念生滅」,既然有生滅,應該也具有虛妄性,蔡老師在哪裏看到、找到一個「不生不滅」的阿賴耶識? 五蘊十八界是可以現前體驗的現象,第八識是幻想的產物,比較兩者,就如同上一篇萬有引力例子中比較樹上的蘋果與幻想的萬有引力,哪一個更真實?當然是蘋果更真實。第八識已經是幻想,它的「不生不滅體性」是幻想之上的幻想。但是在正覺同修會,幻想的東西是真實的,可以「觸證」的;而可以直接觀察到、看到的東西反而是虛妄的。然後再用幻想的第八識,將現前可見的事物變成虛妄,這是否是末法時期學佛顛倒的極致狀態? :禪三的「觸證」就是將屬於「心不相應行」的動作——行來去止,幻想為「阿賴耶識的持身功能」,覺得這個功能非常真實,然後再想象一下五蘊的生滅無常,這就是蔡正禮所説的對比。爲什麽會將「心不相應行」幻想為「阿賴耶識的持身功能」,因爲正覺錯解五蘊、行蘊、「心不相應行」的定義,借用世親菩薩的《百法明門論》發明正覺總持咒,但是不知道《百法明門論》所説的「三位差別」是什麽意思! 正覺獨家發明的「對比真心和五蘊」的説法,套用了佛法名詞,融合「妄想與話術」,可以輕易欺騙很多初學者。爲什麽說這是一種「話術」? 話術是將本來不合理的、沒有邏輯的東西,讓你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的一種「語言欺騙術」。比如蕭平實很喜歡說「以這個真心來看待色身、來看待妄心」、「從實相界──第八識的角度來看、從現象界的角度來看」,這是不懂觀行的人的妄想,爲什麽? 請問如何「從真心來看待妄心」?南伽他師兄曾經指出:「這是凡夫妄想自己能夠站在其他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思惟模式。」 如果我說,我現在「從蕭平實的角度看待某一件事」,如果我就是蕭平實,我不需要「從蕭平實的角度看」,就直接說我是怎麽看待這件事;如果我不是蕭平實,我如何代入蕭平實的思惟看待某一件事情、代替蕭平實發言呢?難道不是我自己幻想「蕭平實是這樣看待某一件事的」? 說「我」可以「從蕭平實的角度看待某事」,只有兩個可能:(1)我真的跟蕭平實合一了,我跟他完全一樣,既然如此,「我(妄心)」不用多此一舉去轉依「蕭平實(真心)」;(2)我(妄心)沒有跟蕭平實合一,只是幻想自己是蕭平實(真心),將自己變成蕭平實代言人、替蕭平實講話。 從另一個角度説,「以這個真心來看待色身、來看待妄心」、「從實相界的角度來看、從現象界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蕭平實常用話術都少了一個主語。請問是「誰」「以這個真心來看待妄心」?當然是「我」或者是「我的意識妄心」! 斷我見的人肯定沒有一個「意識我」可以「以這個真心來看待色身、來看待妄心」,明心的人不會有一個「能看待的」和一個「所看待的」。有「我」、有「能看待的真我、所看待的一切法」,是凡夫的二元對立思維,只是凡夫不會用蕭平實的「佛法話術」將幻想無限上綱,變成可以賣錢的開悟。 琅琊閣痞客幫留言區裏面有明心師兄將蕭平實的話術和觀行「大解剖」,解釋蕭平實幻想的「那個立場」: 「年禪三證悟系列」1 《念佛人到了這個境界,就已經了知真如和妄心的差別》 以那個立場解釋:他清醒位時隨時隨地,可以看見嘴唇周邊肌群在收縮放鬆開合,那就是他說的真如在那裡運作,清晰可見,這就是證真如。第八識以名色所顯,以作用而顯示之,那裡都看得到肌肉收縮放鬆,一縮一鬆現觀永遠如此,那就是真如。 《然後他就以這個真心來念佛》 以那個立場解釋:以真心作用在肌肉一縮一漲,這就是真心功能,但真心非色非心,要在肌肉群上運作,你看到就是慧眼所見,這就是以真心來念佛。 《念佛的時候是念佛的真心》 以那個立場解釋:念佛是真如作用在肌肉群運作,意識清楚知道真心不是肌群,而是無形無色的作用。 《不是念佛的名號、不是念佛的形象。以我真心念佛真心》 以那個立場解釋:慧眼現觀嘴唇周邊肌群不斷很忙運作,從這瞭解八識如何運作機制,叫做觀行,這部分的觀行。 《這個時候,能念與所念都是這個真心》 以那個立場解釋:以八識的立場來看,都是真心,一真一切真。 《不離這個真心,而念諸佛的真心》 以那個立場解釋:諸佛的真心也一樣。 《就以這個真心來看待色身、來看待妄心、來看待時間、來看待一切空間、一切的事、一切的物,都會跟無常、苦、空、無我相應,因為照見真如、真心、自性彌陀,它的真實、不變異、恆常不變,所以相對照之下,色身變得很虛幻,妄心、妄知、妄覺更虛幻。》 以那個立場解釋:因為照見真如始終一如,作用一縮一漲永遠如,現在如,過去如,未來如,無形無色非空非有,作用一如,慧眼現觀即證真如。再從慧眼智見,一真一切真,沒有真妄和合這回事。 以那個立場分享。 :凡夫本身看待事物就帶著大量的妄想和錯覺,學法是糾正和丟掉這些妄想和錯覺,不是給自己增加更多妄想錯覺。當你的「觀行」夾雜大量妄想、推論、幻想,脫離現前、當下、直接的觀察,一定不會看到「諸法實相」,甚至連法的「自相」或「共相」都無法看清楚。 正覺所犯的根本錯誤,可以總歸為一句話:「錯解第八識、第七識,並於二者添加了自己想像的妄想」。以世間精神醫學作比擬,可以稱之為「第七、八識妄想症候群」。「第七、八識妄想症候群」不但是一種邪見,習慣了妄想必然脫離「如實」,這種思惟方式最終會影響我們看待解讀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將我們從一個凡夫變成一個偏執的宗教狂熱份子。 :我最近反思我們過去對觀行的錯解,正覺的「幻想觀行法」有個很可怕的副作用:幻想是毫無邊界、可以無限延申的邪見。 爲什麽我們當初相信蕭平實説可以現觀第七、八識,説到底就是因爲相信了蕭平實的「玄奘轉世」幻想。 當你將這個幻想當成千真萬確,就會進一步接受「如來藏持身、意根做決定」等幻想,長時間生活在這種宗教幻想氛圍裏面的人,一定會滋長更多幻想,比如:佛菩薩給我一念、導師看得見我們的福德(但是看不到許多人的惡行?)、導師過去世是玄奘、大慧宗杲、佛陀十大弟子、我跟導師在西藏被追殺、我跟導師、某師兄師姐是往世眷屬、導師有護法神、親教師很多都是玄奘過去的弟子……張善思師兄甚至可以幻想他不認識的「某人」批評正覺和蕭平實的原因是因愛成恨,然後當成事實、寫成文章發表!這種種幻想,都是長期熏習正覺的「幻想觀行法」產生的嚴重副作用。 蕭平實最近面對張晉榮親教師對他的質疑——尤其是「蕭導師不可能是玄奘」的質疑,就是用宗教妄想推諉、狡辯:「佛菩薩既然已向某些人放出我的來歷訊息,私底下漸漸流傳開來,我也欣然接受,請問您:我能反對嗎?沒有誰可以不接受佛菩薩的指示,乃至等覺、妙覺菩薩亦然。」 從蕭平實的角度想象佛菩薩,佛菩薩當然只能是不可違逆、要求絕對服從的極權帝王! 大豬師兄說正覺同修會自欺欺人,一個患上「第七、八識妄想症候群」的人時刻活在宗教妄想當中,當然時刻自欺,可怕的是,自欺的素材和詭辯(欺人)的素材可以從佛經裏面隨意摘取、套用、加工、附會,你敢質疑他們自欺欺人,他們立刻有恃無恐,搬出「我是接受佛菩薩指示、你是誹謗三寶、你會下地獄」的恐嚇。這樣的「學法」、「修行」,對一個人的人格、對他身邊的所有人、對佛教界乃至整個社會,造成的是什麽樣的影響和傷害? 07.「持身體驗」其實是冥想修定過程常見的「人格解體」? :正覺同修會的個別「明心菩薩」會强調他們有真實的「持身」體驗,這種「體驗」是什麽? 第八識持身是無法體驗的現象,個別人所謂的「持身體驗」其實是攝心和修定過程中發生的「身心分離」現象,西方科研近十年對「正念冥想(mindfulnessmeditation)」的研究裏面有提到這種常見體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jt/5993.html
- 上一篇文章: 于坚密西西比河某处六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