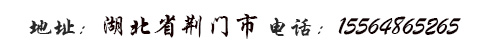爱抚让人愉悦,因为它是一首神经元吟诵的诗
|
沿着由无髓鞘神经元构成的信息通路一路狂奔,我们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畅快的幸福瞬间和最浓情的亲密关系。 StevenMPhelps是得克萨斯大学综合生物学系的副教授。他的实验室用计算机模型和计算分子分析基因的表达方式,致力于研究动物的行为、演化过程和认知能力。他现居奥斯汀。 攻读神经解剖学学位期间,我曾经研究过一颗浸泡在半加仑溶液缸之中的大脑。我们的实验室手册详细绘制出了大脑的结构图:在沿中线切开的爱尔兰老人头颅示意图上,研究人员对一半结构暴露在空气中的大脑进行注释,写清每个部位的作用和功能。我和实验合作伙伴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层层剥开溶液缸中的大脑,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在粗略的解剖轮廓图上进行标注。考试中,老师要求我们在脑桥和髓质的微小分区里找到针尖大小的位置,用图表展示小孩子碰到火炉后瞬间缩手的大脑信息流。这就是神经系统科学的魅力:它像是一本呈现人生百态的地图集,只要一把解剖刀和一双稳健的手,你就可以轻松阅读每一页所记载的精彩内容。 大约一年之后,我和几个研究生一起午后出游,感受溪水在脚踝和腰间自由流淌,用围网捕捉各式各样的小鱼。领队的是一位既固执已见又聪明异常的鱼类学教授。他教会我如何围网:把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以倾斜的角度让渔网在身后的水中随着水流游弋。他向我展示如何在水中移动才能将鱼儿赶到提前布置好的网内。虽然我对捕鱼一窍不通,但他还是礼貌耐心地给我详细指导。我看着在伊利诺伊州广袤无垠平原上蜿蜒前行的弗米利恩河(VermillionRiver)出神时,他突然问我:“你是个神经生物学家,能给我解释下为什么水流如此令人心驰神往吗?” 也许是因为溪流明暗不定,水声潺潺,时而明丽如镜,时而波澜起伏。我没有说出口,而是将这个想法藏在心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教授奇怪的问题和现场尴尬的沉默将会成为未来二十年里我们讨论的重点。 也许我们太过羞于谈论自己的奇思妙想。神经系统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绘制出大脑的“通航水域图”,了解其中的每一条支流和每一圈涟漪。我们对装满爱意和欲望的大脑进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es)。可即便我们绘制出大脑的通航水域图,又有什么用呢?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所言:“你们掌握的那些事实很有用,但是它们并不是我的家园。”为什么瞬间的触碰能让人怦然心动?为什么明明是短暂的接触,却让人感觉像是数十年一样漫长?想要找到值得为之奋斗的答案,我们应该从皮肤入手,以诗歌收尾。 十九世纪末期,苏格兰医生亨利·福尔斯(HenryFaulds)在日本海滩上散步时发现留有远古时代工匠手印痕迹的陶器碎片。使用类似方法制作的现代陶器能够以更出众的方式呈现出制作者的手印痕迹等细节,这让他开始注意人手的微妙差别。当时的博物学家通常喜欢在叶子的表面涂上薄薄的印刷机油墨,然后盖上一张纸,以此记录外国蕨类植物的精美纹路。福尔斯用类似的方法记录了复杂的指纹和掌纹。他发现自己朋友、同事的指纹和掌纹均不相同,存在各种各样的图案模型。 年,福尔斯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自己的发现,提出将手印的特殊性应用到犯罪学领域。他建议用不同颜色的油墨将目标对象的手掌纹路印在玻璃上,通过幻灯机就可以看到两块玻璃上的手印是否重合。从烟灰和血液中采集到的掌纹信息可以用于指控或者排除犯罪嫌疑人,也可以用来鉴别无头尸体的真实身份。 文章发表之后,威廉·赫歇尔爵士(SirWilliamHerschel)很快回应说自己已经开始使用指纹来鉴别孟加拉国囚犯和抚恤金领取者的身份。赫歇尔将自己收集的大量指纹数据送给了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FrancisGalton)。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堂弟,也是统计学的开拓者。他发现指纹在指肚的三角形区域内汇聚在一起,形成无数种排列组合。年,高尔顿比较了的弓形、箕形、斗形纹路。据他估算,两枚指纹完全相同的概率大约是六百四十亿分之一。显然,我们手纹和掌纹的排列组合数量比世界上所有手指的数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出许多。在进化过程中偶然形成的指纹似乎已经成为个体身份的代名词。 指纹如此丰富多样,因此当所有指纹都具有某种特征时,我们就会对其格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aguaa.com/mngjc/6327.html
- 上一篇文章: 小初读影响力16权威与头衔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